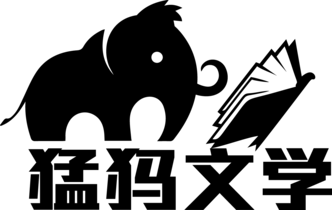第8章 伊莎多拉·邓肯
伊莎多拉·邓肯(1878年5月26日—1927年9月14日),美国舞蹈家,现代舞创始人,世界上第一位赤脚在舞台上表演的艺术家。她的情人多如繁星。林语堂说:“她的一生充满诗意及神秘,不但享过人生的艳福,也尝过人生的苦涩。”
当她跳舞时,她不再是自己,而是女巫、森林女神、女祭司、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的精灵。总之,在舞台上,她完全看不到自己,她与她所扮演的形象形神合一。她就是伊莎多拉·邓肯,开创了现代舞的美国女舞蹈家。
写邓肯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一再想起黑木明纱演过的一部电影——《非常舞者》。她不是作为一个人在跳舞,而是一团火。邓肯生活在一个破碎的家庭,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母亲是个乐手,以教授音乐为生,尽管生活非常拮据,但是母亲依然带着四个孩子独立生活。母亲的强悍、自立、乐观在她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种烙印影响了她的一生。
每个人的身上都带着成长的痕迹。邓肯在童年时期就显露出其独立判断的能力,她从不盲目服从别人,也不肯屈从于利益。最突出的一点是,她对婚姻不抱希望,她从未把精神的快乐和生活的幸福寄托在一个男人身上。
母亲曾经告诉她,世间没有上帝,只有你自己的灵魂和精神才能帮助你。邓肯早期的艺术之路非常坎坷,一位经常观看舞台演出的邻家老妇人看了邓肯的舞姿后,不无善意地说:“世界上最好的芭蕾舞演员是意大利的范妮·埃斯勒,她简直就是个天才。当然,你也跳得很好,你会成为第二个范妮·埃斯勒。”
老妇人的话令邓肯心动不已,同时也打动了邓肯的母亲。母亲带着她去拜访旧金山一位著名的芭蕾舞老师。老师要求邓肯用脚尖站立,邓肯问道:“为何要这样?”老师回答道:“这样很美。”但是邓肯一点儿也不觉得美,她觉得芭蕾舞机械而僵硬,所以只上了几节课就再也不去了。
没有天赋和气质,但我有决心
邓肯认为,芭蕾舞不是她理想中的艺术,真正的舞蹈必须来源于大自然,像海浪的涌动,枝条的舒展,风吹拂的姿态,总之它是不受束缚的,是完全符合人体自然美的,而不是像芭蕾舞那样过度夸张人的身体,将所有舞蹈动作都规范化,装在一个框架里。
为了追求梦想,她和母亲来到芝加哥,拜访了一家又一家剧院,但都遭到了拒绝。剧院经理们的话如出一辙:“小姐,你跳得确实非常棒,但是并不适合舞台演出。”
在当时的美国,流行的舞蹈是芭蕾舞和社交舞蹈,尤其是具有古典色彩的芭蕾舞,几乎一统天下。现实与理想之间总是有差距的,邓肯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她们住在旅馆里,日子一天比一天糟糕,付不起房租,没有饭吃,甚至连行李也被扣了,几乎快要流落街头饿肚子了。邓肯不得不用最后一点钱买了一箱番茄,她们整个星期都在吃番茄,没有面包和盐,母亲虚弱得快要晕过去了。
这时,一个男人出现在她的面前。这个人嘴里叼着粗大的雪茄,帽檐压得很低,他吐了一口青色烟圈儿,用懒洋洋的口吻对邓肯说:“伊莎多拉,你长得很漂亮,舞也跳得很好。只要你愿意跳一些带劲儿的舞蹈,我想我会雇用你。”邓肯想了想旅馆所剩无几的番茄,便答应了。
这是一家三流舞场,留声机里播放着当时流行的《华盛顿邮车》的曲子,邓肯随兴地跳了起来,很多动作都是她即兴加进去的,使舞蹈更加性感诱人,令舞场经理十分满意。他付给邓肯每个星期50美元的酬金。但邓肯只跳了一个星期就不跳了,这令剧场经理非常惊诧。50美元,在当时可是相当可观的收入,但邓肯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因为这件事让她恶心,不要说50美元,即便给再多的钱她也不会干了。她追求的是纯粹的艺术,而不是在低级剧场里混日子。
她说,我既没有天赋也没有才华和气质,但我知道我有决心,决心和热情往往要比天赋、才华和气质更有力量。
邓肯和母亲在旅馆中蹉跎的日子里,无意中在报纸上看到了奥古斯丁·戴利要来芝加哥演出的消息,这令她非常高兴,她决定寻找机会拜访他。戴利是美国著名的剧作家,还经营剧场,旗下有很多明星。邓肯并不认识戴利,但她决定用守株待兔的笨办法。
她守候在剧场的门外,一次次请守门人传达自己要拜访戴利的愿望,最终,她获得了与戴利见面的机会。一见到戴利她立刻开始发表个人主张,仿佛在进行一场演说。她的演说完全将戴利惊呆了,实际上戴利根本没听明白她在说什么,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女人敢在他面前这样讲话。他叫她表演一段舞蹈,结果她获得了扮演一个小配角的资格。
在纽约上演的莎士比亚喜剧《仲夏夜之梦》中,邓肯扮演剧中的精灵。她身穿用半透明的白纱做成的长筒裙子,头上戴着美丽的花环,背上还装着两只特制的金色翅膀。她尽情地跳着,仿佛从山野中来的仙子,不带一点尘俗,充满了自然的原始气息。她的舞蹈获得了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但却遭到戴利的斥责,他认为她把舞台变成了低俗的歌舞厅。在此后的表演中,一旦邓肯上台,戴利就命令灯光师关掉舞台上的主灯,只留下侧灯微弱的光,结果观众几乎看不见舞台上的演员,只能看到一些朦胧的白色影子,若有若无,像黑暗中的精灵在舞动。
在美国几经辗转,邓肯尽管有了一些声名,但是始终没有突破。她认为美国人不能理解她的艺术,她要去欧洲发展,只有欧洲才能理解真正的艺术。1900年,23岁的邓肯到伦敦演出,她身穿宽松的白色长裙,赤着脚,伴随着肖邦的音乐跳着完全由她自己设计的舞蹈。她的演出在伦敦颇有反响,她又决定去巴黎演出,因为巴黎是艺术之都,只有征服了巴黎,她才算获得了真正的成功。
他的眼眸里有星星
邓肯在欧洲有一位影响力很大的支持者——辛格夫人,这位夫人是个同性恋,却0先后嫁给两位亲王,都以离婚告终,但她获得了大量的财产,因而生活十分奢华,经常在家中举办派对和沙龙,她的派对和沙龙云集了当时欧洲的名流和艺术家,邓肯被邀请在她的沙龙上表演舞蹈。
在辛格夫人的沙龙上,邓肯结识了著名的雕塑大师罗丹。59岁的罗丹已经在与卡米耶的恋情之水中退潮,邓肯女神般的自然气质立刻吸引了他。他请求邓肯去他的工作室,他要为她做一尊雕像。
邓肯早就听闻过罗丹的盛名,对他仰慕已久,因而对罗丹的邀请满口答应。他们乘着马车来到罗丹的工作室,工作室有着与这位大师身份相称的规模,简直就像一座宫殿。采光性极好的高大落地窗,阳光从天鹅绒窗帘的缝隙里流泻进来,在质地优良的大理石地板上投下柔和的光影,宽大结实的工作台上放置着琳琅满目的工具、雕塑成品、半成品、素描等。
罗丹请她喝上等咖啡,让她换上宽松的白色长裙,以便跳舞。他请她参观雕塑作品,有老人、小孩、半裸的成年男子、全裸的女子的雕像。他的作品充满了生命力,老人的雕像躯干上凝固着岁月的力量,小孩的脸庞上闪烁着阳光,半裸男性的肌肉仿佛蕴藏着爆发力,裸体的女性仿佛刚刚出浴,散发出一种体香,令人迷醉。他一边向邓肯介绍自己的作品,一边看着她。他的眼睛闪闪发亮,银色的长须流溢着智慧的光芒,邓肯在这种注视中几乎要迷醉了。
之后,邓肯开始赤脚在罗丹的工作室跳舞,她表演了根据古希腊诗人忒奥克里托斯作品创作的舞剧中的一段。舞中的邓肯化作了仙子绪任克斯,躲避着潘神的追求,最终变成了一根芦苇。罗丹看着她的表演,用手中的画笔画了几幅速写,他的眼神追逐着她的舞姿,仿佛要将她牢记在脑海里。邓肯跳完后,向罗丹解释灵感的来源,罗丹似乎完全没有兴趣,接下来发生的事令邓肯大吃一惊,她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他的手在我脖子和胸部游走,抚摸我的胳膊、臀部、大腿和双脚……他揉捏着我的身体就像揉捏着黏土,迸发出的热情将我炙烤融化。
一位欧洲评论家曾在一篇文章里说,罗丹也许是所有雕塑家中最好色的一个,对模特肉体的兴趣和通过作品描绘肉体的天赋齐名。实际上,罗丹从不讳言自己对女人的兴趣,他说,人们说我满脑子都是女人,可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他经常请女模特在他的工作室里跳舞,命令她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出各种动作和姿态,包括嘴唇和眼睛的神态。他对女性,尤其是女性的肉体有着丰富而细致的观察和了解,他作品里的女性的肉体简直比真实的更加诱人,让人情不自禁,甚至引人犯罪。
然而,他的行为显然惊吓到了邓肯,因为此时的邓肯对性毫无经验。她挣脱了罗丹的怀抱,像一头受惊的母鹿,慌乱地披上外套跑掉了,将罗丹一个人扔在工作室。罗丹站在那里一头雾水,不知道做错了什么。还没有人拒绝过他,不论是贵妇还是模特,从未有人拒绝过他。
罗丹没能一亲芳泽,却成了邓肯的铁杆粉丝,只要她在巴黎演出,他几乎从不缺席。他和观众们一起鼓掌,一起呼喊。然而,他的掌声淹没在了雷鸣般的掌声中,呼喊也消失在海潮般的呐喊中,他是那么专注地望着舞台上的邓肯,就像望着一个不可触摸的女神。此时,这个拥有巨大光环、骄傲得像国王一般的老男人的内心是否会有一丝落寞?
多年以后,邓肯在自传中披露了心迹,她非常后悔自己当初的幼稚行为。她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我真是后悔极了,因幼稚而拒绝了他,我没能把自己献给伟大的潘神,了不起的罗丹,否则的话,我的艺术和人生将获益非凡!”
邓肯和罗丹的邂逅没有结局,很快她就陷入了一场恋情。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演出期间,她结识了演员贝列吉,两人很快演绎了一场死去活来的恋情。爱的时候海誓山盟,分手的时候悲痛万分。邓肯身上火焰一般的力量、坚毅的性格、不断变化的脾气以及对艺术的痴狂,有时候使人怀疑她是一个疯子,令贝列吉无所适从,最终离开了她。
爱是眼睛所见的灵魂
很快,她的巡演在欧洲的其他城市确定下来,她马不停蹄地奔走在维也纳和柏林的路上。她在柏林的演出点燃了这座城市的热情,无数疯狂的观众为她呼喊,有的人为她哭泣,还有的人因为激动而晕了过去。大学生们拼命地挤向舞台,最终他们成功地爬了上去,邓肯差一点成为踩踏的牺牲品。演出结束后,狂热的观众抢夺了她的马车,将套马解下来赶走,然后人群替代马匹拉着车,一路呼喊着将她送回居住的宾馆。
欧洲的巡演获得巨大成功,邓肯创立了舞蹈学校,还成立了经纪机构,这一切同时伴随着爱情。
1905年,克雷格闯入了她的生活。这是一个英俊且充满才华的男人,有着白皙的皮肤、匀称的身材和不俗的谈吐,他是一位演员、导演、优秀的舞台设计师。他们几乎是一见钟情,一见面他就拉着邓肯的手上了马车,邓肯甚至来不及告诉母亲她要去哪里,就跟着他去了波茨坦的工作室。
邓肯将克雷格视作另一个自己,而克雷格则将邓肯视作他记忆中的,或者说是他曾经想创造出来的人物。邓肯在克雷格的工作室里待了整整两个星期,放弃了多场演出。包括她的母亲在内,所有人都以为她失踪了,母亲还差一点精神失常,到处打听她的行踪,去了一个又一个警察局,还去了美国驻德大使馆。邓肯的经纪人和剧场经理急得简直要发疯,因为观众每天都在期待她,剧场只好对外放风说邓肯病了,报纸上刊登的消息说,她患了严重的扁桃体炎。
就像胡兰成说的,男的废了耕,女的废了织。邓肯和克雷格两个人待在工作室里,热烈地说着话,几乎没有一刻停息。他们谈彼此的理想、艺术理念,也缠绵于床笫,整日整夜在肉体的欢悦中。
然而,就两人的性格而言,他们并不适合结合。邓肯极端自我,她不肯因为爱情而嫁给一个人,她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反叛者,她为克雷格生了孩子,却不肯嫁给他。
克雷格专断独行,嫉妒心极强,他担忧甚至恐惧邓肯的才华优于自己。他的自尊心有一种变态的倾向,他喜欢她,又嫉妒她,他不能容忍一个女人比自己高明。他不希望邓肯抛头露面,更不要说去舞台上跳舞了。他经常对邓肯说:“为什么不能抛开你的舞蹈?为什么要在舞台上胡乱挥舞你的双臂?为什么不能留在家里,给我削削铅笔?”
邓肯和克雷格的绯闻很快传了出去,就像现在喜欢追逐明星绯闻的人一样,邓肯的花边新闻很快就闹得满城风雨,引起了轩然大波。最激烈的反应来自邓肯创办的舞蹈学校,舞蹈学校董事会的成员包括柏林的一些上流社会的贵妇以及有钱的资助人,给邓肯送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指责她行为不当,并且集体辞去董事身份。
这一行为激怒了邓肯,她在柏林爱乐协会的大厅举行演讲,为自己辩白。她在演讲中侃侃而谈,谈舞蹈精髓和自己的艺术主张,还大声疾呼女性的权利,认为女性拥有自由恋爱和生育的权利。她的演讲获得了一小部分人的支持,而更多的人则持反对意见,因此会场上嘘声不断,最终持反对意见的观众向舞台上扔杂物,将她赶下了台。
邓肯一边参加演出,一边陷在恋情中。她说:“有时候人们会问我爱情和艺术哪个更重要,我的回答是我无法把两者分开,因为艺术家是这个世界上的唯一情人,只有他才能看见纯粹的美。如果允许看一眼永恒美的话,那么爱便是眼睛所见的灵魂。
尼采说,当女人爱时,男人当知畏惧,因为这时她牺牲一切,别的一切她都认为毫无价值。尽管克雷格极端专横(显然克雷格不懂得尼采说的畏惧之意),但邓肯仍然不舍得离开他,直到他们的女儿出生,他们的关系才慢慢好转。大概和母亲的单身状况有关,邓肯认为婚姻是荒谬的东西,爱情和婚姻无关,她不需要通过婚姻来获得一个男人,因此她拒绝和克雷格结婚。
克雷格嫉妒得发疯,因为邓肯几乎每天都沉迷在舞蹈设计中,她的才华像太阳的光芒,令他黯然失色。克雷格怀着强烈的爱与嫉妒心,请求邓肯与他结婚,但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克雷格勃然大怒,一把拉起坐在椅子上的邓肯的女助理,将她抱进房间,并锁上房门。
基于对婚姻的排斥,邓肯决定做一个单身母亲。因此,她很快带着孩子离开了克雷格。邓肯与那些分手后因爱成恨的女人不同,她从不怨恨与自己有过肌肤之亲的男人,甚至不要求孩子的父亲担负任何责任。在她看来,她喜欢一个男人只是因为爱情,不喜欢一个男人同样是因为爱情,和责任、义务以及其他都无关。
对于克雷格,邓肯从无怨恨,甚至可以说她依旧爱他。她毫不讳言说自己对克雷格身体的迷恋以及从中获得的愉悦。她说:“我不知道别的女人是如何回忆自己的情人的,我想,得体的回答应该是说到男人的头、肩膀、手等为止。但是我看见的他,解脱衣服的束缚后,洁白柔软、光滑发亮的身躯照耀在我眼前,使我不能仰视。”
邓肯曾说,一个男人的爱,不同于另一个男人的爱。让人一辈子只喜欢一个人,就好像让人一辈子只喜欢听一个音乐家的作品一样。因此,她很快就有了新的情人——帕里斯·辛格。
辛格富有才华,尤其是富有经商的才华。他拥有豪华的别墅、游艇,为邓肯在巴黎市中心购买了一处非常大的建筑,邓肯又一次实现了创办舞蹈学校的理想。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久,邓肯为他生了一个男孩,却拒绝了这位超级富豪的求婚。她从未将嫁入豪门视作目的,她是一个视金钱如粪土的奇女子,能够让她心甘情愿献身的唯有艺术和爱情。当她意识到自己不爱这个男人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带着儿子离开了他。
“我相信,最高形式的爱是纯精神的激情,不一定需要依赖性。”她如是说。
治愈情伤的唯有爱情
人生如舞台,邓肯的爱情简直就像是在演绎一幕幕戏剧,然而落幕的方式却是悲剧。离开辛格后,邓肯很快又喜欢上了一个意大利男人。1913年,厄运降临在了邓肯的身上。司机开车送她的两个孩子回家时发生意外,车被冲入河中,两个孩子一起死去了。
之后,她的第三个孩子在出生后不久便夭折了,上天再一次剥夺了她做母亲的意愿。她是那么喜欢孩子,她让他们接受最好的教育,为他们买最好的衣服,每天都亲吻他们的脸庞,可是这一切都被剥夺了,她痛不欲生,近乎崩溃,完全沉溺在痛苦悲怆的泪水中。她离开了这个意大利男人。然而,痛苦并没有击倒她。她说:“我用生命里每一份智慧的力量来反抗婚姻。”
她全身心地投入到舞蹈中,继续在欧洲各国演出。她在《舞者之歌》中说:“我将哀伤、痛苦以及对爱情的幻灭转化成我的艺术。”在她的生命中,舞蹈艺术是她唯一永恒的追求,就像是她崇拜的古希腊文化中的酒神精神一样,她将舞蹈视为灵魂必不可少的东西。
能医治爱情之伤的唯有爱情。
她很快就有了新的情人,因为她的恋爱频率过高,一些卫道士指责她是高级妓女,高尔基则认为她是一个拼命取暖的女人。也许是吧,作为一个天才,尽管她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但内心是孤独的。就像邓丽君一样,唱了情歌千首,知心人却没有一个。男人一个个投入她的怀抱,又一个个离她而去,或者说被她抛下,只是因为她发现那不是她想要的爱。爱情是火,没有它会太冷,可是抱得太紧,又会焚身。
邓肯是尼采思想的拥趸,显然也崇拜王尔德,她曾念着王尔德的名言“宁要片刻的快乐,不要永久的悲伤”踏上巡演之路。在俄罗斯,邓肯结识了芭蕾舞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邓肯好像迷上了他,与之往来十分密切。有一天,邓肯忽然亲吻了大师的脖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情不自禁地回吻了她。但这位俄国人远没有罗丹那么勇敢,他被邓肯的热情吓坏了,又担心自己的家庭,逗得邓肯哈哈大笑。
她曾说,天才对我有致命的吸引力。每一段爱情,她都全身心地投入,但每一段爱情都以悲剧告终,随即又投入下一段,像飞蛾扑火,又像一个吸毒者,不可自控。
邓肯的舞蹈征服了欧美,不但风靡于各大剧院,受到观众的疯狂追捧,就连欧洲王室也邀请她去演出。在美国演出时,总统罗斯福也亲临现场。后来,苏联也向她发出了邀请,请她去教授舞蹈。
1922年,邓肯在苏联与诗人叶赛宁相见了,这是唯一一个她愿意与之结婚的男人。邓肯与叶赛宁第一次见面之后,外界就有了两人的八卦,甚至有目击者称:她慢慢向前走来,仪态端庄。用那双晶亮的蓝色大眼睛环顾房间,瞥见叶赛宁时,用目光凝视着他。叶赛宁走过来坐在她的脚边,她用手指抚摩着他金色的头发。邓肯吻了吻叶赛宁的嘴唇,她那鲜红的小嘴带着愉快的语调,吐出一个俄语单词——天使。
凌晨4点,叶赛宁与邓肯携手离去,他们在马车上热烈地交谈着,他们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叶赛宁完全不懂英语,而邓肯会说的俄语仅限于几个可怜的单词。爱情居然有这种奇异的力量,使两个语言不通的人能够燃烧起来。
随着初见的热潮消退,邓肯开始不满足于自己的语言现状,便聘请了一位俄语教师充当自己的语言老师。这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俄语教师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教授她,但她无法接受这种循序渐进的学法,直接问道:“如果我想表达自己的情感,比方说我想亲吻一位漂亮的小伙子,我该怎么说?”邓肯的问题显然将这位老师吓得不轻,她再也不来给邓肯上课了。
“每一次新爱向我走来时,不论是以魔鬼的身份、天使的身份,还是以常人的身份出现,我都相信那是我等待已久,即将复活我生命的唯一的爱。”
1922年5月2日,曾经说过“任何聪明的女人签订婚约之后,还要签订婚约,一切苦果皆是自取”的邓肯与叶赛宁在莫斯科结婚了。一向坚持自由之身,不肯屈身于婚姻的邓肯居然结婚了,当这条消息传到美国后,她的粉丝们震惊无比。
她和叶赛宁很快制订了环游世界的旅行计划,在登上飞机之前,邓肯甚至起草了一份遗嘱,在遗嘱中,她把自己的全部财产留给了丈夫叶赛宁。然而,像以前的所有感情一样,这是一段悲剧性的感情。
叶赛宁性格忧郁,游移不定,令人不可捉摸,有时候兴高采烈,有时候又情绪低沉。对于大他17岁的邓肯来说,他简直像一个任性的孩子。邓肯爱他,宽容他,好像同时在扮演母亲和妻子的角色。她宠爱他,当他故意以命令的口气高声道:“伊莎多拉!拿烟来!”邓肯就赶紧把香烟递到他的手里,并点上火。同样,他又命令道:“伊莎多拉!拿酒来!”她便乖乖地把香槟酒的酒瓶递给他。她满足他的虚荣心,他也乐于玩这种控制与被控制的游戏。
邓肯究竟出于何种原因,要和这个忧郁却粗暴的诗人结合?她绝非一个为了婚姻而奋不顾身的人,她也不是第一次品尝爱情滋味的女人。也许,是因为母性。叶赛宁卷曲的金发,蓝色的像大海一般澄澈的眼睛使她焕发出内心的母爱,在她的心里,她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叶赛宁。然而,叶赛宁却并非听话的孩子,他固然有诗人的激情和才华,但同时也拥有苏联乡间男人的种种恶习,酗酒、蛮横、粗暴,当他发现邓肯手捧着孩子们的相册流泪时,他抢过她手中的相册扔进了燃烧着的壁炉,然后怒吼道:“他们已经死了,你用太多时间想他们了。”
叶赛宁也不喜欢邓肯的朋友,当他发现她把朋友们带到家里,并在家里弹琴时,立即暴怒起来,捡起一个铜烛台扔向镜子,将巨大的玻璃镜击打得粉碎。客人们被他吓得惊慌失措,他咆哮着,怒吼着,将这些客人称作行尸走肉,结果客人们不得不落荒而逃。
1924年,邓肯与叶赛宁的婚姻走到尽头。1925年年底,叶赛宁在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一家旅馆里自尽。叶赛宁的死,对她又是一次残酷的打击。尽管她无法忍受叶赛宁的性格,但她仍然爱他,直到他死,她也未曾和他离婚。她说,我终生都在等待有着美好结局的恋爱故事,希望它永远都不会结束,就像大团圆电影里描写的那样。她一生都渴望做一个妻子、母亲,然而她终究失败了。在才华与命运的抗衡中,她像传说中修真的渡劫者,被雷电之火击中了。
每个人都是熔炉里的一点星火
邓肯离开了苏联,离开了这片孕育了无数艺术家的广袤土地,这也是邓肯的伤心之地。“爱情没有给予我的快乐,我从艺术追求中得到补偿。”
“我宁愿全裸地跳舞,也不愿像当今美国妇女那样,半裸地、带有挑逗性地、装模作样地在大街上行走。人体本身就是一种美,因为这是现实的、真实的、自由的。它应该唤起人们对它的崇敬,而不是恐惧。舞蹈家必须使肉体与灵魂结合,肉体动作必须发展为灵魂的自然语言。”邓肯的舞蹈,是解放身体的舞蹈。她在自己的舞蹈著作中说,所谓女性美,乃是由认识自己的身体开始。
她收集了大量古希腊的艺术品,研究了古希腊陶瓷瓶上的成千上万种人体形象,通过自己的舞蹈,将古希腊时期的精神和意志传播给现代人。她甚至在希腊神殿附近买了一块地,以建造自己的神殿。她总是身穿宽松的白色或者其他颜色的长袍,赤着脚在舞台上跳舞。她的舞姿充满率性、自然、即兴的风格,每个动作都流畅、完美,仿佛就应该是那样。
与芭蕾舞的严谨相比,她的舞蹈唤醒了人们的情感,使人笑,使人哭,使人发狂。总之,她的舞蹈中有一股生命的力量和发自内心的情感。她说:“在一群观看我表演的公众面前,我从来没有犹豫过,我把自己内心最深处、最隐秘的冲动展现给观众。”
与其说她的舞蹈是艺术,不如说是一种宗教。
在艺术与爱情之间,她身上有一条统一的规则。当她爱一个人的时候,她会毫不犹豫地奉上自己的身体,甚至强烈地想为对方孕育孩子,就像把舞蹈连同自己的心奉献给观众。当她不爱一个人的时候,她绝不向对方敞开身体,即便对方是国王。在她的身上,罕见地保持着情感与肉体的统一,那些污蔑她为“高级妓女”的人,并不真正了解她。
1927年8月的一天,她告别朋友,披着自己喜欢的红色长围巾乘敞篷车离开,围巾被卷入车轮,颈动脉被围巾勒住,导致颈动脉断裂,瞬间便香消玉殒。她曾经说:“我们每个人不过是熔炉里的一点星火……它燃着,我们便有形有体;它熄灭了,我们便化为乌有。”我无法想象皱纹爬上她的额头,也无法想象她老态龙钟的样子,也许这是上帝的选择。
所有的牺牲都是要开花结果的。邓肯终身致力于现代舞蹈的普及,她曾骄傲地说:“从芬兰到南美,各国都依据我的思想成立了舞蹈学校。”
后世的人们津津乐道于邓肯与无数个男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就像追星族迷失于偶像层出不穷的八卦中,却完全不懂情感对艺术的价值。伪君子通常恐惧肉体,因为他们胆小虚伪,像行尸走肉一样,否定感官的价值。而纯粹的色欲依赖者则沦陷在感官的迷醉中,成为缥缈的影子。
邓肯勇于表达感官的价值,但同时对感官又有着自己的认识。她说:“我从来没有昏过头。”感官的快乐愈是强烈,大脑的思维就愈是活跃。
邓肯热爱过的男人,宛若星空的明星,他们激发她的灵感,使她重生,当然也带给她巨大的痛苦,爱情成就了她的舞蹈艺术。也许高尔基说的是对的,她是一个需要暖意的人,而她也从这种暖意中找到并紧握住了艺术女神的手,男人就像她的灵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