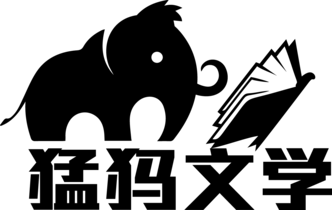第3章
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年4月4日—1996年3月3日),法国作家、电影编导,代表作《广岛之恋》《情人》。16岁时遇见中国男人李云泰,是她第一个情人。25岁与男友的好友结婚,婚内恋上一位美男子,并引荐给丈夫。70岁那年,结识大学生杨·安德烈亚,是她最后一个情人。王小波评价她是“现代小说的最高成就者”。
“他同样有着心理优越感,因为他的财富,和已经侵占了这位白种少女的既成事实。在高档餐厅里,烛光晚餐进行中,他居高临下地笑着宣布,我不能娶你,因为你已经不是处女了。她边抓紧时间狼吞虎咽边同样笑着回答,那太好了,反正我不喜欢中国人。”
杜拉斯在自传体小说《情人》中记述了她的第一个情人——中国情人。正如她的独白:“我在18岁的时候,就已经变老了。”她18岁,或者说从15岁半开始跟这个中国男人游斗,各自显示着属于自己的优越感,彼此需要却互相打压。
男女之间的角逐,莫不如此。布努埃尔的电影《朦胧的欲望》中,肯奇塔一会儿是女骗子,一会儿是纯爱少女,使得马德奥晕头转向,一次次抛弃她,又一次次忍不住寻找她。堂兄问他,你既然这么爱她为什么不娶她?他说:“那样我就没办法控制她了。”他以为自己有钱就可以让她沦为情妇。然而她拿到他的钱后不是逃跑,就是跟年轻的小伙子在一起,使得马德奥一次次地崩溃,而她又回过头来告诉他那只是戏。布努埃尔最终没有告诉我们那到底是不是戏。女人唯一的筹码就是我爱的不是你,而是你的钱。
《一米阳光》中的川夏,每次吵架后都不会忘记拿走年良修递过来的支票。年良修对此耿耿于怀,却不知道她一张都没有兑现过,只是用这个动作来刺伤他。
但杜拉斯没有这么隐晦,她很直接,她的自信让她直接。
在他们做爱的老地方,他给了她一记耳光,将她内裤扯下,用性来发泄并警示她——她依附于他。她在被“强暴”之后,还能够面不改色地问他:“你觉得我值多少钱?”他把钱丢给了她。在光线被门板上的横格切得横七竖八的夜,他对她说:“跟着我说,你来找我,是为了钱。”
她说:“我来找你,是为了钱。”
张爱玲说,没有人会爱上你的灵魂。连男人自己也说,男人是用眼睛来看女人的,而女人是用心来看男人的。用眼睛看到的是物质的,灵魂却需要感受力,要用心去感受。他(中国情人)占有了她的肉体,又开始要求她的灵魂,这所谓的征服从来不是爱,只是虚荣,所以他感到挫败,他自嘲地笑了。
爱情不过一场徒劳
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女人会让男人抓狂。在杜拉斯面前,谁都会输,因为她从一开始就看清爱情虚无的本质。人类倦怠的普遍现状让他们连追求爱情的激情也没有了,只有寂寞、空虚、无聊,所以她不做爱情的囚徒。
杜拉斯说:“爱情并不存在,男女之间有的只是激情,在爱情中寻找安逸是绝对不合适的,甚至是可怜的。”但她又认为:如果活着没有爱,心中没有期待的位置,那是无法想象的。
这仿佛是一个悖论。大多数人都在追求这并不存在的爱情,自欺或者欺人,因为他们总要有一个支撑,保有期待。所以,杜拉斯又用一生去追求爱,只是她的爱情观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她结婚、离婚,非婚生子。她同时跟两个男人一起生活,还不忘跟情人之外的男人偷情。大量的露水情缘滋养着她旺盛的生命力。爱情和写作都是需要激情的活动,她用爱情来刺激写作的神经,又用写作来虏获可以带给她生活激情的男人。源源不断,马不停蹄,在情欲里追逐着。
这似乎是一种吞噬。
从少女时代与中国情人那段爱情故事开始,杜拉斯的一生都是在爱情与写作、欲望与激情几种状态中迂回旋转,就像她小说的写作手法,来来回回,纠结在一个地方。
从21岁在巴黎法学院读书时,她的浪漫史就没有断过。在那时候的人们眼中,她漂亮且放荡,有一种独特的、过于自我的魅力。
1939年,在25岁的时候,她与罗贝尔·昂泰尔姆结婚。罗贝尔如兄长般呵护她,包容她,又如朋友般理解她,与她进行交流。尽管后来离了婚,他仍旧是她信赖的人。他与她的情人迪奥尼·马斯科洛和平共处。
迪奥尼是个美男子,非常美,杜拉斯对他一见倾心,施展全身的魅力去征服他。不久,两人便都爱上了对方。她把他介绍给自己的丈夫罗贝尔,三人关系明朗化。
接下来的10年中,这两个男人先后离开了她。她仍旧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在爱情与欲望中尽情游走。
只一人,爱你哀戚脸庞上岁月的留痕
杜拉斯在70岁的时候认识了大学生扬·安德烈亚。那时她的脸真是“备受摧残的容颜”,她精疲力竭,虽然每年都有作品问世,在法国文坛上有了些名气,但是并不被人欣赏。而且因为长期酗酒,性情乖僻,瞧不起任何一个女作家,尤其讨厌波伏瓦。她总爱说自己如何,如何,还学没落贵族的腔调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让人很是反感,连出版社的人都不喜欢她。
她很孤单,所以扬的出现就如一根救命稻草,使她欲罢不能。她处处控制他,把他封闭在一个小世界里,让他成为自己的专属品。她蔑视他,又离不开他。
她不允许扬在公开场合提到她。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她也很少谈起扬,总是把扬隐匿起来。直到1983年,杜拉斯在医院昏迷不醒,扬发表了《玛·杜》。一直是杜拉斯笔下的人物的扬终于也把杜拉斯变成了他笔下的人物。杜拉斯离世后,他住进了她送给他的房子——位于杜拉斯的巴黎故居对面一幢楼的阁楼,并创作了《这种爱情》。这一次,他把他们所有的生活景况都说了出来:酗酒、写作、乘车沿河散步、毫无目的地东游西逛、疯狂的嫉妒,绝望的情欲以及无法把握的欢乐。
这是一种感情的抒发,仿佛正对着爱人喁喁细语,或疏离、或浓烈,带着没有回音的孤独。正如杜拉斯先前所说:“使我们结合的这种热情,在我不多的有生之年和你今后漫长的岁月中会持续下去。”
杜拉斯在世时喜怒无常,给杨买圣罗兰的衣服,要他洗碗、打字、开车、到海边兜风、陪她看电影。扬27岁,瘦高个儿,羞涩寡言,是个同性恋。她不允许他有任何交往,不允许他看男人一眼,也不允许他看女人。连扬的母亲来了,扬也得偷偷去见,还得掐着时间赶紧回来。
杜拉斯用她独有的小说式语言来对待扬。爱他的时候,她说:“扬,你跟我一起走了吧。”恨他的时候,她又说:“我的东西你一点也得不到,别痴心想要什么了。”
杜拉斯是一个任性的、难以对付的老太婆。她的爱是极度占有,是歇斯底里,如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她就是一直在写自己内心的呼喊,活得恣意任性。然而扬也有受不了的时候。可他只要消失无踪,不留一句话,不打一个电话,杜拉斯就辗转难安了。
每一次,扬都会回来,仿佛她的手里有牵着他的线。
两人就这样在一起生活了16年,直到杜拉斯82岁去世。
她死在他的怀抱里。
有些关系就是这样,相处很难,却又无法分离。
需要也是一种爱情,缠绵不断、沉郁、忧伤,如即将燃尽的蜡烛,在黑暗中流露出些微温暖和光亮。
有一次,杜拉斯带扬出现在公众面前。有一名记者提问:“这该是您最后一次爱情了吧?”她笑着回答:“我怎么知道呢?”
因为孤独,所以写作
杜拉斯言行合一,身体力行,她把自己对爱情的理念放在她的文字里,也付诸实践。她似乎不是在写作,而是在表达自己,恰巧使用了文学这一手段。她说:“我写女人是为了写我,写那个贯穿在多少世纪中的我自己。”她是极其自恋的,用白日梦般杜拉斯式的语言让自己的思绪未加整理便形诸笔端,一种流动的、自由的语言与她心灵微妙的变化相得益彰。
杜拉斯的文字仿佛被施了魔法,对读者有一种吞噬般的魅力,这跟她专注于一种情感而反复摹写有很大的关系,她一生都在创造和感受与性爱有关的事件。
杜拉斯小说里的人物充满无力感,她自己却是情感充沛的。她说:“一个女人若一辈子只和一个男人做爱,那是因为她不喜欢做爱。对付男人的方法是必须非常非常爱他们,否则他们会变得令人难以忍受。我爱男人,我只爱男人,我可以一次有50个男人。”
杜拉斯的爱情充斥着性爱和肉欲,她试图通过性欲的宣泄剥离出爱的最原始的本质,给人一种回归本原欲望的快乐,没有道德的约束,没有虚与委蛇的遮掩。这是近乎纯粹的欲望,干脆直接地抵达爱的核心。被人类打上罪恶标签的欲望从被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回归自然的欲望本身,充满人性的光辉,也不再是痛苦的。
杜拉斯人格的极致解脱体现在她的小说里,对生命的探求以及对女性意识的维护,尤其是《情人》,她完全摒弃男性经验,充分表达女性自身体验和情感心理,从男性文化中脱颖而出,显示出女性的独立和尊严。
“和有情人,做快乐事,别问是缘是劫。”杜拉斯崇尚快乐的原则如李碧华笔下的妖,不必遵守世间人的规矩,蔑视传统道德,揭开了原欲的这美而毒的面纱。她的“自我”通过对他者的开放,最大限度地得到了张扬。在杜拉斯的概念里,爱情是一种能量,它能照亮人的精神和感官。
与精神相对的总是物质,杜拉斯写了《物质生活》。在现实中,物质又是多么重要。因为没有钱交水费,停了水;夏日炎炎,口渴,不能洗澡,她看着一家大大小小的孩子,只平静地微微一笑。于是她带着丈夫、孩子,出了家门,平躺在铁轨上。杜拉斯说:“无知的女人再无知,却也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尽头那不可解决的问题,这是唯一的出路,绝望,同时需要载体。”
她不厌其烦地述说她们的贫穷,甚至用贫穷来标榜白人少女的优越感,以此找到漠然对待肉欲的理由。
“如果她对他有所欲望,他就是她的情人。”杜拉斯极力放大欲望的重心,又不断地淡化“情人”“欲望”这两个词的冲击力。对她而言,情欲如吃饭睡觉一样,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所以她说:“任何人都不能抗拒情欲,它使人上瘾。他们明白它的可怕与强大,然而,每个人都会无可避免地成为它的俘虏,这就是它的魅力。”
不可遏止的情欲源于人心的孤独,所以就有了征服与被征服,越是受到阻碍的情欲越对人有吸引力,情与欲的融合才能达到销魂的效果,否则只是动物般的游戏。孤独在情欲的烘托下显示出酒神状态的本质,所以杜拉斯其人、其行、其笔下的人物蒙着一层酒神的迷醉面纱。
然而,放纵的相拥之后,并没有解决孤独的问题,所以情欲自然而然地转换,她积极地寻找生命的另一个出口。杜拉斯的另一个出口便是写作。
从不取悦,只活自己
有人说:“杜拉斯、波伏瓦、克里斯蒂娃是战后法国知识界最重要的女性,我更喜欢杜拉斯而不是波伏瓦。因为波伏瓦是书斋型的,她很会运用知识,而杜拉斯给你的恰恰是真正情感和生活的部分,这离克里斯蒂娃就更远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情感和生活更能打动人心,而知识只是扮演着工具的角色。
杜拉斯的心溢满情感,源源不断地产生,然后流于笔端,所以她不必去刻意观察生活,不必像福楼拜教莫泊桑一样每天去观察门前经过的马车,不必像达·芬奇那样一个鸡蛋画无数遍,她只抒写自己,自然而直接地,就够了。因为自然而直接,所以来得浓烈,如化不开的云,如醇香的酒,如让人上瘾的罂粟,不由自主地被她拉入她自我经验的个体世界,私人化的世界,那里跃动着强壮的生命力,那里的女性体验是赤裸裸的。
她太自恋了。
她过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过于注重自己的感觉,好像生活在醉生梦死之中,这也是一种生的力量。“我的一生,都在和异于常人的感觉作斗争。”她弱小的身躯时时表现出一种力量感,无所畏惧,心地坦然,这种无所顾忌、勇往直前的态度也让她总是处于极端状态:“在我酗酒以前,我就有了一副酗酒的面孔。”她还说:“当我越写,我就越不存在。我不能走出来,我迷失在文里。”她像个影子,不适合在任何团体中留下痕迹。
杜拉斯不取悦什么人,“真奇怪,你考虑年龄,我从来不想它,年龄不重要。”她没有美人迟暮的叹惜,亦没有女为悦己者容的兴趣,“确实没有必要把美丽的衣装罩在自己的身上,因为我在写作。”
法国的评论家米雷尔说:“承认或者隐而不说,是形成杜拉斯作品风格的魅力之所在:意指的震颤波动。”这种震颤是灵魂的震颤,是模仿不来的。所以有些模仿杜拉斯的人只得其形,也烦琐复杂,反复轮转,终究没有那份直击人心的力量。
她写《劳儿之劫》,就拿出全部的感受力,捕捉一丝一毫的情绪波动,再投放到劳儿身边所有的元素上去,劳儿被人化的物包围着,也就是被她的情绪包围着。所以,不必叙述劳儿的男友是什么样的人,不必叙述她被抛弃的过程,只渲染了一种气氛,一个孤魂野鬼般的女子在行走,不停地行走就够了。略去所有老套的情节,读者只需感受这无限延展的细腻情绪,朦胧、细碎,既没有结构,也没有细节,所以显得那么不可捉摸,不可理喻。
她的自恋达到自闭的程度。写作是孤独的,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任自我无限膨胀。贫苦的童年、印度支那的记忆、腐败的殖民地,她的哥哥和母亲和那没有希望的日子……
她要逃离这一切,她终于逃离了这一切。她拼命地写作,她来到法国,她制作电影,扛着摄像机在诺弗勒堡到处走,摄制组的一群人围着她。他们一起出工,拿一样的报酬,她给他们熬葱汤,煮越南饭,她曾进入生活。那时她拍过《印度之歌》《巴克斯泰尔,薇拉·巴克斯泰尔》《卡车》和《夜舟》。很多年后,杜拉斯又记起这段时光,就送了一本《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给曾经合作过的剪辑师,亲笔题词(这是少有的情况):“给我的朋友多米尼克·奥弗莱存念。往昔的奇迹,今朝依旧,为一同致力于电影的岁月。”
对于杜拉斯来说,电影是写作的延续,“我把电影视作写作的支撑。无须填写空白,我们在画面上挥毫。我们说话,并且把文字安放在画面之上。”她厌恶商业电影,厌恶煽情,她的电影是作家电影,是写出来的,自主、自足、小成本、小制作。长长的画外音加上沉闷的“黑镜头”,更像是书写的空白,给人一种荒芜、沉闷的感觉。
那时候的杜拉斯默默无闻,直至1984年《情人》出版后,才轰动法国,继而名震全球,终于成了名副其实的“杜拉斯”。
1996年3月,杜拉斯辞世,葬在巴黎蒙帕纳斯公墓。
她说:“任何一个女人都比男人神秘,比男人聪明、生动、清新,从来也不想做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