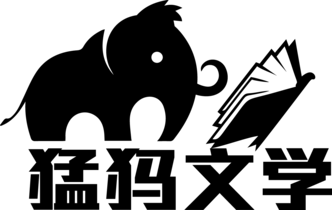第2章 乔治·桑
乔治·桑(1804年7月1日—1876年6月8日),法国著名小说家,一生创作244部作品,是巴尔扎克时代最具风情、最另类的小说家。她与文学大家缪塞的过往情史,与音乐大师肖邦的同居生活,成为19世纪法兰西文坛的佳话。
有人说,女人更容易出名,写点东西就让人觉得很了不起。这不是对女人的额外优待,而是潜在歧视,似乎女人就是没有头脑、没有创造力的族群,能够写作就可以让男人惊诧了。这种想法之所以根深蒂固也不是没有缘由,遍翻文学史,无论西方与东方,与一长串的男性作家的名单相比,女诗人、女作家确实少得可怜。19世纪的法国,出现了一个乔治·桑。
雨果曾评价:“她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其他伟人都是男子,唯独她是女性”。而且是一位独具风情的另类女性。“乔治·桑”本是一个男人的名字,而她原名叫奥罗尔·杜邦,为了行事方便,也为了避免众人对女作家的诟病,她给自己取了一个男性名字。她喜欢把自己打扮成男人,喝烈酒,抽雪茄,骑骏马,周旋于众多追随者中间。
她同时拥有四个情人
奥罗尔的父亲是拿破仑的部下,军官杜邦。母亲是波希米亚人,曾做过皇宫里的服装工人。在她4岁时,父亲坠马身亡,母亲迫于生计,沦落风尘。祖母怕有过风尘史的母亲带坏了小奥罗尔,就把她接到乡下诺昂同住。
祖母是萨克斯元帅的私生女,一心想把孙女培养成淑女,13岁时就把她送进巴黎修道院。奥罗尔是贵族血统和平民基因的混合体,从小就抱有民主信念。她曾经写道:“我是贵族父亲和波希米亚母亲的女儿。我将和奴隶、波希米亚人站在一起,而不是与国王和他们的走狗们在一起。”
怀着对爱情和婚姻美好的憧憬,18岁的奥罗尔与贵族青年卡西米尔·杜德望结婚,成了男爵夫人。但是杜德望平庸乏味,与浪漫多情的奥罗尔不甚和谐,她很快就厌倦了丈夫。虽然在当时的法国,婚外情已经成为时尚,但是像她这样丢下丈夫,带着两个孩子与情人一起到巴黎生活的女子却几乎没有。她的“离婚”属于创举,有惊世骇俗的味道,因为那时的法国上流社会还是很保守的。
1832年,奥罗尔在巴黎出版了第一部小说《安蒂亚娜》,于是变成作家乔治·桑。她是最早以稿费为生的女作家之一。乔治·桑的文采很快引起巴黎文化界的注意,身边经常围绕着许多追随者,有诗人缪塞,作曲家兼钢琴家肖邦和李斯特,文学家福楼拜、雨果、梅里美、屠格涅夫、戈蒂耶、小仲马和巴尔扎克,画家德拉克洛瓦、柯罗……甚至包括拿破仑的小弟弟热罗姆·波拿巴亲王。其中有些人成为她的情人。她在从祖母那继承的诺昂庄园里接待这些高朋,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由此可见乔治·桑的文化层次。
曾经有一段时间,她同时有四个情人,所以,她也曾被人们指责为放荡、叛逆。乔治·桑却说,一个像她这样感情丰富的女性,同时拥有四个情人并不算多。她借自己的作品公开宣称:“婚姻迟早会被废除。一种更人道的关系将代替婚姻关系来繁衍后代。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既可生儿育女,又不互相束缚对方的自由。”
乔治·桑蔑视传统、崇尚自由,不为成规所束缚,那还是在“女权”这个词并未成形的年代。她的思想在如今这个时代也是超前的。
她最著名的两段感情是与浪漫主义诗人缪塞的纠缠以及与音乐大师肖邦的缱绻。
在爱情中,越投入,伤害就越大,越投入,就越在乎,越在乎,就越抓住细枝末节不放。纠结、撕扯、质问、争吵、报复、背叛、结束、再轮回。仿佛存在一个临界点,每个在爱情中沉沦的人都要达到这个点,或者越过去,或者失败而返。
写小说的人还会靠理智生活,写诗的人则完全靠感觉生活。缪塞的神经质和歇斯底里时表现得像酒鬼一样疯狂,倒使乔治·桑顾及了秩序和现实,但是也快被他逼疯了。
因为迷恋,所以受伤
1833年7月,乔治·桑与缪塞在一次晚餐会上相遇。遇见谁都自有道理,人就像个磁场,总是吸引与自己相近的那个人,所以尽管他们一开始并不信任对方,却仍旧走到了一起。
乔治·桑比缪塞大6岁,在她的眼里,他就是一个浪荡不羁的花花公子;在他的眼里,她太过“才女”味了。乔治·桑曾对准备主动充当介绍人的圣伯夫说:“经过考虑,我不希望您把阿尔弗雷德·德·缪塞介绍给我。他太风流,我俩不合适,我之所以想见他,更多的是出于好奇而不是感兴趣。”她被自己的理智蒙蔽了,其实她在潜意识里对缪塞是有向往之心的。
在第一次见面的晚餐桌上,他们兴致勃勃地谈论文学及各自的创作。过后她又让他把未完成的作品《劳拉》的一个片段寄给她。缪塞要求说:“请您别与任何人分享您的小小的好奇和任性。”如此两人便拥有了一个共同的秘密。之后缪塞又把自己的作品寄给乔治·桑,并写长信说这是读了乔治·桑的《安蒂亚娜》后写成的。他在信中借小说暗示了一种暧昧关系。
有些人第一次见面就会有一种超自然的感觉,就知道两人之间会发生点什么。所以,尽管乔治·桑说出了“我俩不合适”那样的话,但是她已经预感到她与缪塞会有故事发生。她的小说《莱莉亚》中的斯泰尼奥就是以缪塞为原型。斯泰尼奥沮丧、绝望、忧伤、纵欲,有自杀倾向,正是诗人缪塞的特点。乔治·桑从缪塞的作品中了解到他是怎样一个人,也从他的作品中看到了他们的结局,然后把这种现实又放到自己的小说中去。小说中的莱莉亚怀疑爱情,对生活冷漠,而斯泰尼奥则用对爱情坚贞不渝的热情呼唤着她。
有时,不知是生活创造了小说,还是小说引导了生活。两人的恋情跟着小说情节燃烧,而生活的点点滴滴成为新的小说的素材。也许这就是充满艺术的人生,艺术可以预示命运。
乔治·桑是个有双性气质的人,既有女性的温柔又有男性的力量,而缪塞却很女性化、孩子气,正如弗朗克·莱斯特兰冈在《缪塞传》中所说:“阿尔弗雷德·德·缪塞敏感的气质兼有女性的多情和男性的粗犷;他的感情经历充满激情和痛苦,始终被幻觉与死亡的阴影笼罩。他是缪斯所钟爱的孩子,也是爱情的殉道者。”
对现实生活中亲近的人,天才那颗敏感的心是把双刃剑,缪塞生活在自我伤害的幻觉里,所以给身边的人带来麻烦。乔治·桑如她的小说人物莱莉亚,扮演着母亲的角色,但是,她终究只是他的情人。
太过迷恋对方,难免互相伤害。爱情之所以消耗人的心力,是因为它不像亲情那样保险,不像友情那样淡如水,它充满了动荡不安的因素。强烈的排他性让爱变得自私、暴躁,随之而来的就是嫉妒。而人心又是飘忽不定的,无法专注于一人,尤其是像乔治·桑这样感情丰富的女人。
诗人亚历山德罗·波利奥来访,乔治·桑对他有了好印象。这种心灵上的小小的不忠,在乔治·桑和缪塞的爱情发展到高潮的夜晚第一次引起缪塞的疯狂。他陷入幻觉,在谷底惶恐不安,浑身痉挛,用一种尖厉而猛烈的声音叫嚷道:“咱们快离开这儿。”他以为自己被弄到一片坟地,其实那不过是如墓碑般平坦的岩石。
为了不至于在爱情中沦陷毁灭,他们决定换个环境,边旅行边写作,于是去了威尼斯。一到威尼斯,乔治·桑就生病了,但为了维持生活还是坚持写作。缪塞却因为她不能专心陪他而发脾气,也因为之前的游离心存怨恨,有一次他竟然说:“乔治,我弄错了。我其实不爱你。”
这是很让人心碎的话,但是乔治·桑并非一般女子,她的理智和坚强让她确定缪塞只是负气,如果离开她,他恐怕活不下去。因而,她并未在伤心之下出走,只是关上了连接两人居室的门。
爱情会死,人却要活下去
没有打倒乔治·桑,缪塞就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他不但不照顾生病的乔治·桑,反而留恋风月场所,因伤寒和酒精中毒而病倒了,乔治·桑像母亲一样照顾他。可乔治·桑越对他好,他越觉得她是有愧于自己,背叛了自己。他占有性的爱情把乔治·桑推开。
乔治·桑与帕杰洛医生日夜照顾缪塞,不觉对帕杰洛医生生出爱恋,又一次背叛了缪塞。缪塞独自回到巴黎。乔治·桑留在威尼斯,希望可以继续与缪塞保持联系。她说:“今后谁来照顾你,我又去照顾谁呢?谁还需要我,从此我又能关心谁?你曾经给过我幸福,你也曾给过我伤痛,这一切我怎么可能舍弃呢?但是我们就这样心甘情愿地分手吗?我们不是做过多次徒劳无益的努力吗?每当我们孤身独处的时候,我们那充满傲气和怨恨的心不是被痛苦和悔恨撕得粉碎吗?在放弃这种已经不可能继续维持的关系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永远保持联系。”
他说:“你叫我走,我就走了。你叫我活下去,我就活着。”
他还说:“相隔这么远,再也不会有粗野,也不会有神经质的歇斯底里。”
她说:“我抽超长的烟斗,我几乎孤独一人生活。”
他说:“你告诉我,你要离群独居,你要想念我。当我读到这样的字眼时,你要我怎么办呢?你倒不如告诉我,你已投入了一个你热爱的男人的怀抱,并和我谈谈你们的欢乐。不,别跟我说这些。你不如直接跟我讲,你另有所爱,你也得到了爱。这样,我就会感到自己充满了勇气,请求上帝把我的痛苦都化为你的欢乐。那么,我会感到孤独,永远的孤独。你跟我谈健康,谈保重,要我对未来充满信心,你要我平静下来。是你,是你刚把我的血管切开,而你又要我止住血液,不让它往外流淌!我把自己的青春搞成什么样了!我又把我们的爱情变成什么样了?”
分开的日子,没有了争吵、伤害,却有反省、安慰、祝愿,看起来是平静的,其实是折磨得更深了。在祝福的同时,他们互相推远对方。这种表面的骄傲和坚持只会让对方伤得更深,而得到对方认同的答案时,又伤害着自己。这是一种煎熬和折磨。
他们把这种感情写进了各自的作品,缪塞写了《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乔治·桑写了《私人日记》。
一年之后,乔治·桑回到巴黎,两人相见,爱火重燃,帕杰洛医生悄悄地离开了。有人说,真正的爱情可以冲破千难万阻,无论如何都会在一起。可那只是外界的原因,最可怕的阻碍并不是来源于外界,而是在他们自己身上。习性不除,只会一次又一次地互相伤害、游离、嫉妒。他们再也受不了互相的折磨了,他们的关系最终还是破裂了。
我一直以为真正的爱是没有置换性的,必须是一生一世的,是完结不了的,是任何伤害都无法终止的。原来伤害的力量远远大于爱的力量。
所以,内心强大比爱情更重要,比什么都重要。爱情会死,人却要活下去。
无论是缪塞还是肖邦,都在爱情破碎后郁郁而终。只有乔治·桑是爱情中的强者,因为她是用理性活着的人。她在信中说:“不过我知道,我感到我们会一辈子相爱,心灵相通,志趣相投。我们将会凭借圣洁的感情,努力治愈彼此因对方而受的痛苦。唉,不,这不是我们的过错,我们不过听随命运的安排而已。我们那种粗暴、激烈的性格妨碍我们去过普通恋人的生活。
“请不要以为,阿尔弗雷德啊,不要以为,我想到失去了你的心,还能够觉得幸福。我是你的情人或是你的母亲,这都没有多大关系。我激起你的是爱情或是友情,我与你在一起是幸福还是不幸,这一切都不能改变我目前的心境。我知道我爱你,这就是一切。可我并非带着那种时刻要拥抱你,必须置你于死地我才能得到满足的痛苦心情去爱你,而是带着男性的力气以及女性的爱的全部温柔去爱你的。”
她的爱不像他们的爱,非要置对方于死地,才能满足自己的痛苦心情的爱。绝对的占有和绝对的忘我都是爱,是爱到极致的两种表现形式。乔治·桑更像圣母,而缪塞更具人间烟火气。有时候,我在想,圣徒的“爱情”算是爱情吗?
乔治·桑在小说《她与他》中对缪塞和肖邦的缱绻之情都作了回顾和描述。人们对此颇有争议。但是,一个作家的作品要征服人心,她的生活必定不是平庸无奇的。她不能建筑空中楼阁,不能在象牙塔里写作,她的生活就是与这个世界的连接。雨果说:“乔治·桑就是一种思想。她从肉体中超脱出来,自由自在,虽死犹生,永垂不朽。啊,自由的女神!”
在男人面前,乔治·桑是女神而不是公主。她温柔地纵容任性的缪塞,慈祥地呵护纤弱的肖邦。
你是我生命的缺口
乔治·桑比肖邦大6岁,或许她母性力量太强,所以总是吸引孩子型的男人,以满足她母性的欲望。
那年她32岁,李斯特介绍肖邦给她认识。因为都是巴黎文艺界的名人,在认识之前,两人对彼此已有耳闻,当然乔治·桑来巴黎的时间比肖邦早,这时候她已经跟小说家雨果、画家德拉克洛瓦、诗人海涅等名流相交熟稔,而且巴尔扎克、缪塞总是在乔治·桑的乡间别墅里度假。与乔治·桑相比,肖邦还只能算是新进名人。
当肖邦第一次看到乔治·桑后,他对李斯特说:“她真的是女人吗?我不禁怀疑!”在女人堆里混惯了的肖邦还是被这个男性化的女人征服了。沙龙女主人、公爵夫人、富家小姐,还有众多密友,在他的生命中穿梭而过,只有乔治·桑进入了他的生活。
他们一起生活了9年,分手两年半后,肖邦累倒在巡回演出舞台上,临终时说:“多想再见见她啊!”但是她拒绝了,背过身去独自哭泣。她太倔强了。爱得越深,伤得越深,肖邦成为她最后一个爱人。那年她43岁,之前她身边从未缺少过男人,但是自从肖邦走后,她便独自生活,直至72岁时去世。
总有一段感情刻骨铭心,总有一个人无法超越。也许之前一段又一段艳事都只是激情,是肖邦让她进入爱情的核心。从她的小说《她与他》中可以看出,她对缪塞的尊敬远不及肖邦。可见这个不善言辞、不喜欢写信的男人有一种力量,比那个任性的孩子更加吸引乔治·桑。女人不会爱上让她怜惜的男人。她疼惜缪塞,但欣赏肖邦。缪塞的激情满足了她的爱情欲望,而肖邦的力量充实了她的思想和生活。
在乔治·桑与肖邦之间,力与反作用力是平衡的。她感觉到的爱,恰恰是她给予他同等重量的爱。
肖邦一生最爱的人只有乔治·桑一个。自从离开乔治·桑,肖邦没有再写过一首曲子。爱情让人心碎,甚至心死。分手后的那一年,他曾写信给朋友:“如果我不每天吐血,不为眷恋旧情所苦,我可能会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我不再有忧伤和欢乐,不再真的感受什么。我只是浑噩度日,耐心等待我的末日。”离开乔治·桑,他失去的不仅是爱人,还有母性的关爱和智性的督促,他的整个生命仿佛破了一个缺口,失衡了。
彼此相关,又各自独立
他们相遇时,肖邦正处于失恋状态,忧郁、消沉,是乔治·桑重新燃起了他的热情,并把他引领到诺昂庄园,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爱。这个男性化的女人,对这个女性化的男人正好是一种补充。他的忧郁和伤感在乔治·桑独有的爱情方式中被一扫而空。
诺昂庄园是在辽阔草原上的一幢石头房子,四围风景优美,时时传来牧羊人的歌声。这一切都使肖邦心旷神怡。住在这里,他再也不用为生计奔波。以他病弱的身体,依靠教课和偶尔向出版商出售作品所得收入去支撑在巴黎的房租、仆人、衣服等庞大开销是不可能的。如今,他可以安心创作了。而且,乔治·桑周围那一大群作家朋友,对他的创作也产生了极有利的影响。他的创作进入全盛时期。如果没有乔治·桑,他卓越的才华未必能这么容易地开花结果。
在9年的时间里,乔治·桑被肖邦的家人视为“女保护人”,对肖邦极尽关爱与呵护。肖邦在离开华沙后,长期和父母姐妹保持通信。他在信中一再提及自己的灵感来源、音乐会,以及在诺昂庄园里和乔治·桑的生活。
乔治·桑爱护着、珍视着这个天使般的天才,因为她懂他。她说:“肖邦是个天使。他的善良、温柔和耐心有时让我担心。我觉得这是一个太纤细、太完美的天造之物,难以持久存在于我们这个粗笨和沉重的人间。在马略卡,他病得死去活来,却创作出充满天堂气息的音乐……”她对音乐的挚爱和对肖邦才华的赏识,让他们的爱情超越了寻常情爱。她知道这个天才不能屈服于肉体的粗糙。他要寻找的,并非是情妇,而是爱的陪伴。
这位生命力旺盛的女子只能像圣女般地生活,压抑自己的欲望。她曾向友人提起过:“他病得太重了,以致他的爱只能是柏拉图式的。”他们是灵魂之友,是非占有式的。完全的无私奉献,让这种爱具有宗教般的力量。在这9年中,不只是肖邦的创作力被激发出来,乔治·桑也获得了非同往日的灵感。
他们并没有长期住在一起,而是保持着一种奇特的关系。彼此相关,又各自独立。他们的关系既像是朋友,又像是恋人或夫妇。即便是他们同居的日子,也互不干涉各自的社交生活。夏日,肖邦总是去诺昂庄园和乔治·桑一起过一段日子,其他时间则在巴黎公寓里。两人相伴不离的日子是一起在马略卡岛的那段热恋时光,那是两人在一起最长的一段时间。
如此契合的一对恋人,又为何分手?
肖邦不像缪塞那样张扬、我行我素,是个比较内敛的人。而乔治·桑喜欢高谈阔论,有什么说什么。争吵的时候,肖邦的沉默自抑无异于一种冷暴力,让她难堪却无能为力,只能付出更多的容忍。然而容忍不是正常的情感状态,会积压成怨。
她曾在小说里发泄:“他的身心都很柔弱,但是由于他的肌肉不发达,反而有一种动人的美,一种超越年龄甚至性别的外貌,像一位颀长而忧郁的女人,永远沉溺在他的白日梦中,缺乏现实感……此外,他有强烈的占有欲,专制、暴躁、嫉妒……因为他柔弱,于是他会用一种虚伪漂亮的睿智来折磨他所爱的人。他傲慢、矫饰、故示高贵、厌恶一切……”两人性格相去甚远,更加刺痛肖邦的心,但是一向隐忍,甚至有些“虚伪”的肖邦并未表现出来,照常写信问候,表示依恋。
肖邦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活在自己的心灵世界中,国家、民族似乎是离他很远的事。不管外面发生了什么事,他照旧过自己养尊处优的日子。乔治·桑总是批评他缺乏现实感。他只关心自己的乐谱能否出版,音乐会能否举行,这与乔治·桑的整天谈论国事的沙龙实在不大协调。不过肖邦也没有必要这样做,毕竟他是外国人,在法国不能发展他的理想时可以选择离开。
家事的分歧和混乱让肖邦的病情恶化,而乔治·桑也开始倦怠。肖邦的元气几近耗竭,生命沉入黑暗。李斯特这样描述他:“自1846年开始,肖邦几乎不能行走,每次上楼都要忍受窒息之苦。从此,他只是仗着格外小心才得以活下来。”
1846年11月肖邦离开诺昂,乔治·桑关上了接待他的门。
游戏人间,一切都能推翻再来
1848年,在玛利昂尼夫人家,肖邦和乔治·桑不期而遇。当时她正在下楼,距离上次见面已经整整一年了。肖邦强自镇定地问道,“你好吗?”
她答道,“很好。”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一年零七个月后,抑郁的肖邦因肺结核、心脏病死于巴黎。在弥留之际,这个背负巨大才华的男子低声叹息道:“她对我说过,我只能在她的怀里死去。”然而,最后在身边的人不是她,而是那些默默爱慕他的女人。乔治·桑没有参加肖邦的葬礼,甚至不愿再谈肖邦。她让人烧毁了自己写给肖邦的全部信件。她无法保持淡然,唯有恨的抱怨,因为她也被痛苦和失意折磨着,开始怀疑、愤怒。她在心里对他说:你不再爱我了。
“不再爱”是伤人的。
两人全面决裂源于对乔治·桑两个孩子的态度。肖邦无法容忍乔治·桑纵容她的儿子,而乔治·桑受不了肖邦过分袒护她的女儿。她给肖邦写了一封言辞十分激烈的信:
“我宁愿看到你加入敌人的阵营,也不愿看到你在曾经吸我乳汁长大的孩子面前攻击我……我已经受够了作为一个易受欺骗、常做牺牲者的滋味……我不要再忍受这种奇异的颠倒。再见,我的朋友,我将为这九年专情的友谊获此结局而感谢神,希望常常能得到你的消息……”
也许,这也是“不再爱”的缘起,她怀疑他与自己的女儿产生了感情。
但无论如何,乔治·桑是个充满力量感的女人,内心强大,能够给予而不是索取。她只要你给她一点,而她可以给你全部。这是怎样的自信和强悍!她的内心盈满了爱,所以可以源源不断地给予。这正是她与卡米耶的不同之处。她曾给朋友写信道:“我心里有一个目标,一种使命,换句话说就是激情。写作靠的就是这股激情,无比强烈,坚不可摧。”她不但靠激情写作,也靠激情活着。
她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也是一个多情的女人。
她一生写了244部作品,包括小说、戏剧、杂文、书简、回忆录、政论文章。她的小说关注女性生存,认为女人不应该成为男人情欲的发泄对象,女人也有自己的七情六欲,应该主动地得到满足。
乔治·桑与很多大师有交往。她的魅力吸引他们,她与他们的灵魂交错。她与法国作家福楼拜的通信多达482封,两人的世界观存在着某种趋同性。福楼拜对她充满敬意,在自己的新书上题写献词:“向乔治·桑献上一个无名小卒的敬意。”
乔治·桑去世后,福楼拜为之流泪。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每个人都应该去好好了解她,就像我一样。她是天才,是伟人,又兼具女性的万般柔情……”除了福楼拜之外,乔治·桑还受到法国其他大师的尊敬和爱慕。
巴尔扎克在给昂斯卡夫人的信中提及,他打算请乔治·桑为自己的小说《人间喜剧》作序。不过当时她正在病中,未能完成这一托付。乔治·桑也受到巴尔扎克的影响,曾打算像他一样写一个系列小说《人间牧歌》。
大作家雨果被流放泽西岛时,乔治·桑就发表宣言支持这位智者。同样,在1859年乔治·桑的作品《她与他》引来一片攻击的时候,雨果也给予她声援。作家之间建立起的这种友情,不止是惺惺相惜和彼此的尊重与敬意,甚至还有爱慕。雨果在给她的信中曾写道:“我发现我已经爱上了您,幸亏我已经老了。”
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朋友,他就是什么样的人。正因乔治·桑寻求的是灵魂的高蹈,她才获得了这一切。
乔治·桑从来不会把这些写入书中,她只是为了好玩,她永远拥有少女的初心,游戏人间,所以一切都能推翻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