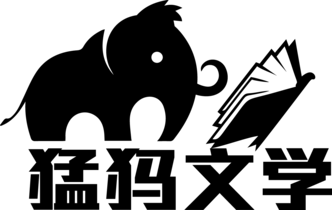第4章
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1861年2月12日—1937年2月5日),一位征服天才的女性。她是俄罗斯流亡贵族的掌上明珠,拥有质疑上帝的叛逆,是才华横溢的作家,也是特立独行的女权主义者。她为尼采所深爱,受弗洛伊德赏识,与里尔克同居同游。
与杜拉斯的沉浸相比,莎乐美是片叶不沾身。
她就像高高在上的女王,俯瞰着匍匐于脚前的臣子。对此有一个非常形象贴切的故事:狂傲的哲学家尼采被第二次拒婚后,提议要和莎乐美、保尔·里一起去照张相,作为他们友谊的见证。在摄影棚里,他让摄影师推来一辆小车,请莎乐美跪在车上,又让摄影师做了一根鞭子,递给莎乐美。而他自己和保尔·里站在车前,用绳子把胳膊绑在车把手上,成了拉车的马,让莎乐美抽打。摄影师大声抗议说这不成体统。尼采解释说,没有比这更好的姿态能表明他们三人目前的关系了。
显然,尼采和保尔·里被莎乐美“掌控”着。
瞬间就能征服旁人灵魂的女人
保尔·里也是一位思想家,学识渊博、思想深刻,却不像尼采那么桀骜不驯、性情乖僻、难以相处,是个宽厚且温和的人。在德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人马尔维达·封·迈森堡夫人的沙龙里,19岁的莎乐美与他相遇。两人很快达成默契,成为很要好的朋友。对莎乐美来说,保尔·里是一个可信任的朋友,像哥哥一样关心她、保护她。
但是保尔·里有自己的想法。他已经爱上了这个“长着一双闪烁着光芒的蓝眼睛,那高高的额头后面是积极的、令人敬佩的思维”的姑娘。终于有一天,这个理性哲人像个绅士一样跪在莎乐美面前,向她求婚,可是被莎乐美率直地拒绝了。她说,她到国外来是为了求知而不是结婚。
求知与结婚并不矛盾,这显然是借口。保尔·里受伤了,决定离开罗马,离开这个伤心地。莎乐美反对他这个想法,她说:“男女之间除了做夫妻、做情人,就不能做朋友了吗?”她希望他留下来,一起实现她的求知梦。善良的保尔·里很容易就动摇了,似乎有点饮鸩止渴的意味,还很大度地建议把朋友尼采也请来。
莎乐美早闻尼采的大名,欣然同意。于是,尼采收到了保尔·里热情洋溢的信:“她充满了活力,天资聪颖,具有最典型的姑娘气质,而且还有点孩子气。”同时,尼采还收到了马尔维达夫人的信,“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姑娘。我的书《一个女理想主义者的回忆录》要感谢很多人,其中就有这个姑娘。”
尼采欣悦的同时,却又不无傲慢地回信说:“代我向这位俄国姑娘问好。考虑到我在未来10年中想干的事情,我需要她。婚姻是完全另外的一章,我至多只能忍受两年的婚姻。”哲人的口气太狂妄了,他还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简直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不知道他的朋友是否把这封信给莎乐美看过,她要灭一灭他的威风?
她照样要见他,一切都等见了再说。果然,见到这位俄国姑娘时,尼采顿时惊呆了,脱口而出“这是一个瞬间就能征服一个人灵魂的人”。
他的灵魂被征服了,便立刻向她求婚,但是被她拒绝了。莎乐美爱慕他的思想和智慧,但是也看到了他的独断专行,不想让自己陷入婚姻的枷锁与暴虐的王国。
浪漫无异于玩火自焚
尼采并没有放弃对莎乐美的追求。他自负地说:“莎乐美具备高贵而睿智的心灵,而且有鹰的视觉和有狮子的勇气。她一定愿与我肩负起人类精神的十字架,走一条上升之路!”
莎乐美在尼采的居处陶顿堡写信给保尔·里:“总体上说,尼采是一个有着坚强意志的人。然而单方面看,他又是个极其情绪化的人。同尼采谈话是十分惬意的事情,你一定也知道这一点。在这种有共同理想、共同感觉的交谈中,常常会心有灵犀一点通。”
心意相通是爱情的前奏,朦胧的爱情已经存在了。
尼采热情引导,莎乐美快意相随,连她的家人都看出来她恋爱了。莎乐美的母亲说:“尼采先生的财产还不够养活自己,你跟他去喝西北风?”尼采如此耀眼,为何还一直没有结婚?莎乐美的哥哥怕妹妹上当,告诫她说:“作为大家闺秀,须知形象第一,名誉第一,人言可畏,浪漫无异于玩火自焚。”
莎乐美的逆反心理显露出来,义正词严地说:“我既不追随典范去生活,也不奢求自己成为谁的典范,我只为我自己而生活。我的生活中没有不可逾越的规则,而是有太多不可言传的美妙的感受,它们蕴含于我自身。在喧闹的生活中,越受压抑越要呼喊出来。”
越是压抑,越要挣脱,莎乐美只要做自己,挣脱追随典范去生活。其个性跃然而出了。在她的概念里没有不可逾越的规则,打破一切,摧毁一切。这不也正是尼采的观点吗?莎乐美是女人中的超人,却比尼采更彻底、更自然。她把这种理论应用到生活中,拒绝纠结、拒绝痛苦。生活在她这里成了体验的过程。她尽情地享受着“不可言传的美妙的感受”,不让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种规则为难自己。
与智性相当的朋友一起游山玩水,不啻为一桩赏心乐事。夏天,莎乐美与尼采、保尔·里一起去阿尔卑斯山。尼采与莎乐美登上了萨库蒙特山,有了单独面对的机会。也许他们尽情地谈论了哲学、人生等话题,但是否谈及爱情却无从考证。想必是超越了友谊的界限,莎乐美在老年时曾回忆道:“我是否在萨库蒙特山吻过尼采,已记不清了。”她说这句话时的口气多么温馨啊,可见她对尼采是动过真情的。而尼采对此更加自豪:“萨库蒙特山,感谢你让我拥有了人生最美妙的梦想。”莎乐美为尼采构筑了人生最美妙的梦想,但梦想如肥皂泡,转瞬化为乌有。
尼采第一次见到莎乐美时曾兴奋地说:“我们是从哪颗星球一起掉到这里的?”他还说:“我相信,我们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年龄。我们的生活和思想是多么的一致。”
莎乐美对这种极致的“一致”也很激动,曾写信给保尔·里,说他们心灵相通。保尔·里难免吃醋,但仍摆出得体的样子。尼采得了便宜还卖乖,怂恿保尔·里去娶莎乐美,声称:“我是一个厌世者,一想到生儿育女的世俗生活就心存厌恶。还是你娶她吧,她正是你孜孜以求的伴侣。”
另一个嫉妒者就没有这么善良了,而是使出嫉妒的阴毒来。她就是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尼采。她一直认为自己才是尼采的知己,看到莎乐美逐渐取代自己的位置,哥哥对别的女人意乱情迷,不由得恨怒交加,挖空心思中伤自己的对手。
尼采一向自诩是思想界的“哲王”,伊丽莎白就看准这一点进行猛烈的攻击,讽刺他的思想越来越带有莎乐美的色彩,感慨他被那个俄国女子的个性控制了。尼采的骄傲瞬间被击中。绝不盲从的莎乐美坚持相反意见,尼采就怒火中烧,拂袖而去。妹妹的煽风点火让他的自负心不断作祟。这对兄妹终于让莎乐美受不了了,在日渐萧瑟的九月,莎乐美踏上归途。
生活没有你,依然美丽
两人已分手,伊丽莎白却仍不罢休,声称“莎乐美与弗里德里希交往纯粹出于卑劣的虚荣心,而哲学家从未爱过她”。莎乐美一气之下,便与这对兄妹恩断义绝。
有些人生来是不受气的,莎乐美不会也无须为爱情忍气吞声,更不愿在尼采的强力下失去自我和自由,所以她在写给尼采的诗中说:“生活没有你——依然美丽。”
尼采也自我安慰道:“一个真正的男子需要两种不同的东西:危险和游戏。因而他需要女人,当作最危险的玩物。”
相对来说,莎乐美要大度得多,在最后这首诗里,她除了安慰自己,还希望对方好好的,“你也同样值得生活下去”。尼采却在给保尔·里的信中骂她:“我以为已找到一位能帮助我的人。当然,这不仅需要高超的智力,而且还要有第一流的道德。相反的,我却发现了一位只想玩弄我的人。她不害臊的是,梦想把地球上最伟大的天才作为她玩弄的对象。”
接到这样的信,保尔·里难免心里犯嘀咕,我是不是只是一个被玩弄的对象呢?当然,这也是尼采受到无可挽回的刺激后做出的强烈反应,因为莎乐美离开他没多久,就与保尔·里在柏林同居了。
她可不像乔治·桑那般好耐性。似乎凡事都要求个“凭什么”,凭什么我就得容忍你?她随时可以走,关系随时可以中止。男人对这类骄傲的女子得小心翼翼,而尼采确实有些张狂,任性妄为,我行我素,没有珍视这份来不之易的感情,当失去的时候才悔之不及。“爱情永远没有我的骄傲重要”,莎乐美只是会伤人,而不会被人所伤。
在莎乐美与保尔·里同居的日子里,他们既不像恋人,也不像夫妻,生活平静无波。这种绵软无力的生活不会是莎乐美喜欢的,所以当那位东方语言学家安德烈亚斯以一种狂暴的姿势闯入他们的生活时,这种平静就难以为继。
安德烈亚斯几乎没有给莎乐美缓冲的机会,登门便求婚,且以步步紧逼的方式。优雅和迂回的求婚都被莎乐美拒绝过,但这一次的求婚,让她有点措手不及,竟然应允了,只是提出两个条件:第一,她必须保持与保尔·里现有的友谊和生活方式;第二,这只能是一桩没有夫妻生活的婚姻。安德烈亚斯答应了。保尔·里却无法理解,难以接受这种关系,所以选择不辞而别。
18年后,保尔·里的死讯传来,他从悬崖上坠落,那正是他和莎乐美曾经共同旅行的地方。莎乐美不由心惊,当即猜到他是自杀,可见离开她后他是如此绝望与孤独。
有人说,“莎乐美并未感到良心不安,她认为良心不安是软弱的表现”,也有人说她为此悔恨终生。我想,自责是有的,伤痛是有的,后悔却未必,因为她没有责任为了别人牺牲自己的选择。
安德烈亚斯恰恰是不会让莎乐美为婚姻做出任何牺牲的人,这从他答应莎乐美的两个条件就可以看出。这段无性婚姻维持了43年,直到他们的生命结束。这种奇特的婚姻方式不仅给莎乐美安定的感觉,还使她保持了自由。其间,她创作了几本书,思想录《与上帝之争》和小说《露特》,还发表了一些评论性文章,以超前的写作手法和与众不同的思想观念在当时的文学界引起轰动,在欧洲赢得广泛声誉。
折断我的双臂,我仍能拥抱你
大诗人赖纳·马利亚·里尔克也慕名来信,在信中表达了对莎乐美的敬仰和钦慕,希望能见见这位“著名女作家”。那时,里尔克还是个年轻的后生,没什么名气,因此在众多来信中,莎乐美并没有对这封信特别在意。
直到有一天,他们在一场沙龙相遇。在见到莎乐美的那一刻,里尔克就为她的美貌和独特的高贵气质而倾倒,之前的崇拜自然而然地转化为爱慕。他用诗人的激情向莎乐美发起爱情攻势,像个孩子一样,任性而直接地哀求:“我不要鲜花,不要天空,也不要太阳,要的唯有你。我要通过你看世界,因为这样我看到的就不是世界,而永远只是你、你、你!只要见到你的身影,我就愿向你祈祷。只要听到你说话,我就对你深信不疑。只要盼望你,我就愿为你受苦。只要追求你,我就想跪在你面前。”
莎乐美不可能对这如火如荼的告白无动于衷。尼采太骄傲,保尔·里太内敛,也许只有这样敢于表露自己,敢于让对方看到自己真实的内心的人才更容易被接受,才最具有征服的力量。而且,里尔克无意间击中了莎乐美的母性情怀,使她想起自己17岁时对吉洛牧师的呼唤。此时的里尔克也正如年轻时的她需要被呵护,她怎能任他一个人在黑暗中挣扎。或许这就是天意,她向他敞开了情感的门。
1897年,莎乐美36岁,她比里尔克大14岁。对于这段关系的发展,她是谨慎考虑过的。她已到了理智制约情感的年龄,并没有像里尔克那样激动。第二天,莎乐美没有如约到剧院,里尔克失魂落魄,捧着玫瑰花在慕尼黑城里漫无目的地游走。
里尔克是诗人,莎乐美不是。她是用理智生活的人,是非天才不与之交往的人。她需要的是灵魂对话,只有天才的头脑才能跟得上她的节奏。她也具有很强的识别能力,当看到里尔克的情书时就曾预言:“多么细腻而内敛的灵魂,他会大有作为的。”
莎乐美的自信、乐观感染着生性忧郁、伤感的里尔克,她广博的学识让他们的生活充满智慧之光。她还建议里尔克去大学听课,劝导他从空洞的内在宇宙转向自然和真实世界。但她从不去扰乱里尔克敏感的内心,只是使他的诗歌由主观的抒写转向更辽阔的境界,从而能够包容世间万物。
他们旅行、会友、野餐、打猎,讨论哲学、诗歌、人生、宇宙,他们精神相通,心灵相契,身体也不可分了,实现了真正的灵与肉的结合。如此和谐,如此美妙,莎乐美这一次真正体验到了作为女性的全部内容。莎乐美在回忆录中认真地写道,“如果说我是你多年的女人,那是因为,是你首先向我展现了真实:肉体和人性那不可分割的一体,生活本身那不可怀疑的真实状况”。
莎乐美回故国俄罗斯,由丈夫安德烈亚斯和里尔克陪同。外人也许会觉得,这“三人行”有些尴尬,但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是正常的。里尔克在异国获得了写诗的素材,莎乐美则做了一次生命的回归。
1900年,三人开始第二次俄罗斯之行。此行他们收获颇丰,结识了一大批文学界与艺术家的名宿,包括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列宾、老帕斯捷尔纳克等。多年以后,里尔克与老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小帕斯捷尔纳克,也就是通过《日瓦戈医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位成为至交。
在俄罗斯之旅中,里尔克认识了俄罗斯女诗人玛琳娜·茨维塔耶娃,他们之间柏拉图式的恋爱也始于此。
“三人行”的生活并非完美无缺。莎乐美在身边,里尔克就能写出饱满而充满灵性的诗歌来。而她一旦回到丈夫身边,他就会陷入孤独和痛苦,灵感枯竭。一开始莎乐美会安慰他,但是久而久之,她感到被束缚,也认为这种依赖对里尔克的创作没有好处,所以决绝地提出分手。
莎乐美刺伤了里尔克的心,她做事一向快刀斩乱麻。在最后一次见面时,莎乐美塞给里尔克一张包牛奶瓶子的纸,上面写了几行潦草的字:“在很久以后,如果你的情况不好,那么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这儿就是你的家。”
虽然最终分手,但这一次的爱情是刻骨铭心的,他们的灵魂从未分开过。在之后的20多年里,他们一直保持通信。据说,在他们的感情最热烈的时候,里尔克曾吟诵道:
弄瞎我的眼睛,我还能看见你,
堵住我的耳朵,我仍能听见你,
没有脚,我能够走到你身旁,
没有嘴,我还是能祈求你。
折断我的双臂,我仍能拥抱你——
用我的心,像手一样。
钳住我的心,我的脑子不会停息,
你放火烧我的脑子,
我仍将托举你,用我的血液。
里尔克的热情是灼人的,莎乐美也在回忆录《生命的回顾》中宣称:“我是里尔克的妻子。”或许他才是她真正意义上的男人,吉洛牧师、尼采、保尔·里和安德烈亚斯都是浮光掠影罢了。
莎乐美与前面几个人的爱情都是因爱生嗔。而莎乐美仿佛像掐着时间,每一段爱情到该结束的时候了,按下按钮就结束了。她的过于理性化使她缺少了些人情味,然而可能正是这种冷冽成就了诗人。莎乐美就像一个擅长预言的女巫,里尔克最终夺得了诗界的桂冠,成为名副其实的诗歌之王。
莎乐美是一个对人对己都要求极高的人,身上有一种积极的向上的力量,在精神与生活方都要求完美。如果是下坡路,她会毫不犹豫地中断。所以,她在50岁的时候,仍旧在求知,仍旧充满生命的活力,把这一年当作一个新的起点。
表面热闹,内心孤凄
这是1911年的秋天。
莎乐美在精神分析学大会上遇到弗洛伊德。她此前就对心理学感兴趣,如今被弗洛伊德的演讲震撼了,就一定要拜他为师。她认为心理学有助于了解人的内心中更深层的东西,帮助自己排忧解惑,对文学创作也十分有利。但是弗洛伊德拒绝收她当徒弟,也许他觉得莎乐美只是凑热闹,不过是游走在上流社会的名媛,什么事都爱插上一手。精神分析学是多么高深啊,哪是她能介入的?
面对弗洛伊德的嘲笑,莎乐美既没有怨怼,也没有放弃,而是用6个月的时间学完精神分析学的基础课程,再去维也纳拜访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这次竟迫不及待地收下了这位徒弟,原因是莎乐美说要同时向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学习。阿德勒是弗洛伊德的死对头,在阿德勒门下学习的人休想成为弗洛伊德的学生。
莎乐美的天真、冒失,古灵精怪,尤其是幽默感吸引了弗洛伊德。另外,心胸不怎么宽阔的弗洛伊德也不会甘心让一个有着超群悟性和过人才智的人成了别人的学生,最终同意收莎乐美为徒。。
后来,这门新学说也确实让莎乐美开阔了视野,对人及人的内心世界有了更深的理性认识。她曾撰写过《性爱》和《物质的爱情》,探讨人们所避之犹恐不及的性意识,不过当时的认识并不深刻。现在她可以利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把这些早已闪现于脑际的思想挖掘得更深。
莎乐美很快在精神分析学界赢得了一份赞誉,但是她与弗洛伊德的关系止于师生,没有由崇敬发展成爱慕。他们之间确实成了她一直要求的那种“体贴的兄长,信赖的朋友,没有一丝异性吸引”的关系。这在莎乐美和男人的交往中是不多见的。
莎乐美与弗洛伊德没有爱情关系,却俘获了弗洛伊德门下最有才华的弟子维克多·陶斯克。而当陶斯克想要稳定和永恒的时候,莎乐美再次离去。她要保持对自己的忠诚,所以不会忠于任何男人,因为忠于某个人的意志,无异于践踏自己的意志。在莎乐美看来,爱情只是风暴,只是彩虹,只是海市蜃楼,想把它固定在婚姻的框架中是不现实的,也是不明智的。恋爱中的女人犹如一棵等待闪电将其劈开的树,要么牺牲自我,要么对男人“不忠”。
很多年以后,陶斯克有了自己的诊所,却在结婚的那天,将脖子伸进窗帘的拉绳套,开枪自杀。作为精神分析专家,或许陶斯克还是对婚姻持传统观念,认为婚姻是神圣的事情,他要的那个人必须是特定的“那一个”,他认定的那一个只能是莎乐美。若换一个,就是用了替代品,是对爱情和婚姻的玷污。
这是第二个因莎乐美自杀的男人。或许成就自己有时要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正如萨特所言:“他人即地狱”。意志与意志之间很难并行不悖。莎乐美对弗洛伊德说:“可怜的陶斯克,我曾爱过他,自认为了解他,却从未想过他会自杀。这种死亡的方式既是一种暴力行为,同时也是一个承受过巨大痛苦的人的最佳选择。”她的这种言论也许会被某些人指责为冷酷无情,但换一种角度看也不失为一种智慧。
莎乐美是弗洛伊德家的常客,但她对大师的观点也不是盲目地全盘接受。从弗洛伊德与荣格的决裂看,弗洛伊德也是个容不得异己的人。不过对于莎乐美的不同见解,他总是给予称赞。他认为她是对这门学说理解很深的人。莎乐美虽然没有自己独创的观点,但能用自己的语言复述大师们的思想,还发表了一些关于精神分析方面的论文,甚至在弗洛伊德的帮助下开了一家心理医疗诊所。
弗洛伊德的书架上一直摆放着莎乐美的照片。两人20多年来一直通信。当时正值关于精神分析学会的大论战、大分裂时期,所以他们的通信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后来莎乐美写作《师从弗洛伊德》一书,也成为精神分析学历史的重要文献。
此前她还写了关于里尔克的书《赖纳·马利亚·里尔克》和尼采的书《弗里德里希·尼采及其著作》,而她的《与上帝之争》中也有尼采的影子。德国作家萨尔勃曾评价莎乐美,说她是一位“具有非凡能力的缪斯,男人们在与这位女性的交往中受孕,与她邂逅几个月,就能为这个世界产下一个精神的新生儿”。
在天才的行列中行走的同时,莎乐美是否忽略了背后那个默默无闻的丈夫?这样异于常人的关系也并非完美无缺。他们的婚姻经常濒临崩溃,却似乎被一股强大的力量黏合着。她曾试图为丈夫另找一个女人来代替自己,他却只要她一个人,因为无人可以代替莎乐美在他心中的位置。他要的就是她,不可以是别人。这种激烈的方式如当初一样,那股蛮劲不是刻意为之,而是精神上的始终如一,非如此不可。
他们老了,在感情上开始需要对方,需要彼此依偎。“为什么从前就不能像如今这样给对方更多一点了解自己的时间?”他们惋惜地叹息着。安德烈亚斯比莎乐美大15岁,于1930年去世。失去丈夫,莎乐美第一次感到了孤独的可怕。他们彼此依存的关系由来已久,只是因习惯视而不见。忽然想到钱锺书的小说《猫》,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游走在男人堆里的李太太忽然有一天被告知,一向沉默寡言、百依百顺的李先生跟一个女孩子走了。她忽然觉得自己老了,身体仿佛塌下来,风头、地位、排场像一副副重担。疲乏的她再挑不起,不想再为那些无关紧要的人维持年轻、美丽、骄傲了。她能在外面风光无限,是因为后面永远有一个支撑、依靠的人。他能让她踏实,让她可以勇往直前。对于莎乐美而言,如果安德烈亚斯一直在,她或许永远不知道孤独的滋味,不知道“伴侣”对她的意义。
7年后,76岁的莎乐美因糖尿病引发的尿毒症造成心脏不适,继而停止了跳动,与世长辞。
莎尔美的女友爱伦·德尔普曾指出,她在莎乐美身上看到了饱满充实的人生所必备的三种激情:对爱情不可遏止的追求,对真理不可遏止的探寻,对人类苦难不可遏止的悲悯。正是这三种激情使她成为魅力无穷、独具个性的尤物,那些傲睨人间、不可一世的天才也只得纷纷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为她迷狂,为她痛苦。
莎乐美的另一位朋友、瑞典的精神疗法医生希尔·比耶尔也曾特别指出:“莎乐美可以在精神上对一位天才全神贯注,却不能彻底与之融合。这或许是她生命中真正的悲剧。她渴望从自己强烈的个性中解放出来,却得不到拯救。从某种深层意义上说,莎乐美是一位未曾获救的女人。”
行走在边缘就不能体验极致的愉悦,或许这就是太聪明、太能跳出感情、永远无法彻底沉浸的人的悲哀。莎乐美无法与人融合,表面热闹,内心孤寂。她用与天才的交手驱遣她的孤寂,或许还有一丝虚荣心。
莎乐美的孤独与尼采的孤独不同。她是强悍的,且能够平静地活着,不会大悲大喜,大伤大痛,久而久之沦为机械化的人。她以完美的外在吸引人,却无法让自己的内核与对方交融。她在享受自我的同时,也失去了另外一部分的快乐。或许,这就是人的局限。
有时候我会想,假设尼采真的与她在一起,像淘一口古井,深不见底,以为埋藏着宝藏,可是淘啊淘啊,仍旧深不见底,一生都淘不到最底层的东西,他会不会很失望?其实井底什么也没有。这也是为什么她从小给人的印象有点孤僻,落落寡合,心智非常早熟的原因。她是用脑子活着,而非心灵。她的脑子装满了知识,对知识的渴求成了她的支撑,内心却如黑洞般匮乏,需要源源不断地浇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