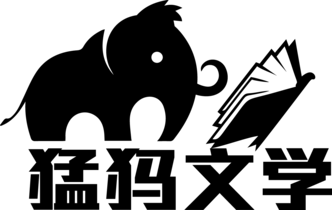第5章
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1806年3月6日—1861年6月29日),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受人尊敬的诗人之一。15岁骑马时不幸跌伤脊椎,从此下肢瘫痪24年。39岁结识小她6岁的诗人罗伯特·勃朗宁,爱与希望使她成为诗人。
“当我拥抱着你的时候,我仍然想你。”
男女之间究竟有没有这种感情?勃朗宁夫人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勃朗宁夫人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负盛名的女诗人,但她不是天生的诗人,是希望和爱情使她成为诗人。
勃朗宁夫人婚前的名字是伊丽莎白·巴雷特·莫尔顿,父亲是种植园主,在英格兰伍斯特郡拥有五百英亩领地——莫尔文丘陵。这片土地充满典型的英格兰风情,少女时代的巴雷特经常牵着心爱的英国纯种马,从别墅的马厩里出来,沿着芬芳四溢的花园墙壁踱步,出了花园大门,她就飞身上马,去拜访领地周边的朋友们。
巴雷特生来体弱,但是她热爱大自然,莫尔文丘陵地区分布着大片的森林、开阔草地和美丽的湖泊,简直像是童话中的王国。她有10多个兄弟姐妹,都脚踏实地地接受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教育,他们要么一起在别墅里排练家庭舞台剧,要么去丘陵区采集植物标本。
总之,15岁之前,她享受着贵族小姐的全部特权,同时又没有旧式贵族的繁文缛节。然而15岁之后,生活急转直下,她就像是戴上锁链的天使,一下子坠入了黑暗的深渊。
那一年,她骑马出行的时候从马背上摔下,脊椎受伤,从此便委身病榻,再也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行动了。
巴雷特就像被黑女巫梅尔菲森特诅咒过的公主罗拉,从此陷身于黑暗中,只有王子才能拯救她。命运真的为她安排了一位王子,那就是小她6岁的罗伯特·勃朗宁。当然,此时她并不知有这样一位男神存在,就像村上春树的小说《1Q84》中的川奈天吾和青豆雅美,两个并无交集的年轻人在各自的世界里生活,然而他们之间却存在某种神秘的联系。
“总有一天我会在什么地方遇到他,是偶然的。我只想静静地、珍重地等待着这个时刻。”也许,少女巴雷特心中未尝不怀着对这种遇见的期盼,因为孤独以它特有的形式折磨着她。当孤独足够强大,它就像是一种酸液,腐蚀着人的心灵。也许是为了抵御孤独,巴雷特选择了阅读。
我要找到你,无论南北东西
从莫尔文丘陵的湖边吹来的晨风拂过玫瑰园,玫瑰的香气飘进了巴雷特的窗子,她尝试着坐起来,却引起背部一阵的剧痛。疼痛使她沮丧,也使她愤怒,她奋力将手中的诗集《失乐园》扔向窗外,却因为力量太小,书籍只砸中了窗前的仿中国花瓶,花瓶摔碎了,瓶中已经干枯的蔷薇花四散在地,暗红的花瓣带着一种祭奠的气息。
早先这个季节,她总是拿着一本诗集在花园里看,就算是没有阅读的打算,她在花园里的时候也总是带着一本书。她收集花瓣和有美丽叶脉的植物落叶,将它们夹在用苏格兰纸印制的诗集中。植物的叶子干透,像标本一样美丽,散发出的水分在书页间留下下斑驳痕迹。现在,那些叶子的标本还在,她却再也不能收集这些标本了。也许,她也成了一种标本,虽然保留着叶脉分叉的天然美,却已经脆弱不堪,轻轻一碾就碎了。
她越想越愤怒:“我什么也做不了,就连扔一本书的力气也没有。”女仆听到花瓶打碎的声音,赶紧走了进来,将地上的书捡起来放置在床边的桌案上,并很快清扫了地上的碎瓷片,连同散乱的花枝和凌乱的花瓣也一并清扫了。
“我只是一个残废的病人,一个残废的女人。”她绝望地想。对她来说,青春就像干枯的蔷薇花,尽管还有一丝鲜亮的色彩,却无一丝香气,是徒具花魂的标本。对她来说,生命的意义只剩下对孤独的反抗、咀嚼、反刍和吸纳。
对于一个内心柔软且丰富的人来说,孤独的意义究竟何在?在正常的环境里,大多数人不会主动寻求孤独。精神健全的人都能与外界联系建立人际通道,这个通道包括与固定的对象建立亲密关系,更进一步就涉及爱。一个人有爱的能力,意味着他在其他方面也是健全的。同样,当一个人刻意寻求孤独,可能意味着他建立亲密关系的通道受阻。但是,处在巴雷特这种环境,她是否被动地处于隔离状态呢?没有,因为有人爱她。
巴雷特的父亲虽然严厉,却很关心和重视子女们的教育,他为女儿聘请过多位语言教师,他们不但教她学习系统的英文课程,还教她学习拉丁语。巴雷特对语言有极高的领悟能力,她能阅读大部分拉丁语作家的作品,还自学了希伯来文,可以毫无障碍地阅读《旧约·圣经》的篇章。
当然,她也绝不会绕开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她追崇但丁,欣赏弥尔顿,当她缠绵病榻的时候,是弥尔顿的《失乐园》和但丁的《炼狱》安慰了她,他们唤起了她对生命的热情。她还阅读伏尔泰、托马斯·潘恩以及女权主义先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作品,后者的《女权辩护》对她影响极大,使她对女性权利有了新的认识。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认为女性并非天生在思维与行动能力上低于男性,只有当她们缺乏足够的教育时才会显示出这种不足,是教育不足导致大部分女性缺乏正确的认知。受到充分教育的女性,不只是男性的妻子,而且能够成为他们同等地位的伴侣。女性需要的不止是外貌和举止,还需要心灵的塑造。她还批判了卢梭“女性无须理性教育”的观点。她认为男性和女性同属于有理性的生命,人类可以在理性之上建立男女平等的社会秩序。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作品使巴雷特认识到,男性地位的产生并不是天然的,而是家庭在教育上更加偏重于男性,进入社会后,男性的接触面更加广泛,接受的思维训练远比女性多。女性长期受不到良好的教育,即便是受教育也仅限于狭窄的范围,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交面也非常狭窄,就连地位较高的贵族和富商家庭的女性也不例外,而普通女性的生活面就更加狭窄了。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她们丧失了塑造心灵的可能,从而变得愚蠢而无知,精神无法独立,只能任人摆布。在经济上,女性受制于家庭和婚姻,婚前从属于父母,婚后是两个家族联姻的产物,财产上受制于丈夫,这就导致经济无法独立。文学作品和女权主义的读物大大拓展了巴雷特的精神世界,她逐渐成为一个思想独立的人。
巴雷特20岁的时候,盲教师博伊德来到她的家中,教她学习希腊语,从而掀起了她对希腊戏剧的热情。她如饥似渴地阅读荷马、品达、阿里斯托芬的戏剧作品,古希腊剧作中燃烧的因子点燃了她本就敏感的内心,她开始尝试诗歌创作。如果说,此前她受到了理性主义的塑造,获得了强大的内心,那么希腊戏剧则使她重获活力,追求真实和激情。这时候,她的身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而且情绪也开朗了很多,经常当众朗读诗歌,并在仆人的协助下参与社交活动。
不是死亡,是爱
大约在1832年前后,巴雷特父亲的生意遭受打击,卖掉了莫尔文丘陵区的别墅和土地,举家搬迁到伦敦温坡街50号,在这里她首次以真名发表了自己的诗歌《天使及其他诗歌》,此后她陆陆续续有诗作面世。
这一段时间,巴雷特的身体时好时坏,家人认为德文郡的海滨气候有助于她的疗养,因此,由她最喜欢的哥哥爱德华陪同她去那里。然而,爱德华却在游泳时溺死,这使巴雷特非常悲痛,精神几乎崩溃,长达几个月,她躺在床上,足不出户,身体也大不如前。在此后长达五年的时间里,除了家人,她几乎不见任何人。她仿佛睡美人一样,重新回到了黑暗中,只有一个人能够解救她,那就是她的王子。就像沉睡的罗拉一样,只要菲利普王子轻轻一吻,她就能立刻从黑暗之牢重回光明的殿堂。
在伦敦阴暗潮湿的天气里,温坡大街50号的房子仿佛一座幽暗神秘的地穴,从泰晤士河上吹过的风带来了大海潮湿咸涩的气流,穿过门廊,进入窗子,湿润着巴雷特的脸颊。她望着窗子上充满维多利亚风格的精细垂花的雕饰,一朵绯红的云正装饰在檐口的肋状物上。此时的她就像古希腊神话中被献祭给海怪克托的埃塞俄比亚公主安德洛墨达,被铁链绑缚在海岬的岩石上,巨浪翻涌,波涛中闪现着海怪克托狰狞的触手。死亡就像这海怪的邪恶爪子一般,随时会夺走她的生命,而她还从未领略过生命的美好。
1845年的5月,巴雷特的朋友约翰·凯尼恩介绍了一位名叫罗伯特·勃朗宁的诗人给她,起初巴雷特与勃朗宁只是通信,但很快他们就见面了。勃朗宁就像童话里的菲利普王子,打败了黑女巫,又像希腊神话里的宙斯之子珀耳修斯,打败了海怪克托。总之,她获救了,她被勃朗宁拯救了。
勃朗宁读过巴雷特大部分已发表的诗歌,对她充满钦慕和爱意。而此时巴雷特已经39岁了,不但罹患重疾,而且因常年卧床形容憔悴,她不相信这个30多岁的青年会爱上自己。
人在年轻的时候会迷失于对崇高理想的仰望,比如爱情和道德,会过高估计理想的力量。一旦踏入婚姻的大门和现实的沟壑,是否还能用仰望的心态来平视拥有的一切?实难预料。因此,当勃朗宁向巴雷特求婚时,她虽然欣喜但仍然拒绝了。实际上,不止是巴雷特自己对勃朗宁的求婚缺乏信任,就连她的父亲巴雷特先生也充满怀疑,坚决反对。
勃朗宁并未因受挫而灰心失望,他写出了一封又一封洋溢着炽热的情书,一次又一次向巴雷特表达爱意,证明他不是因为冲动而求婚,也不是因为渴望爱而昏了头,他是在理性的思考之后做出的决定。
巴雷特仿佛受到了神的启发,她不再将自己锁在房间里,不再做一个精神上的隐者,她决定离开那张依赖了多年的床。起初,巴雷特允许女仆将她抱到户外晒太阳,之后便在仆人的搀扶下开始蹒跚走路,最后她居然可以抛开仆人走到大街上去了。
面对勃朗宁炽烈的爱,她说:“如果到了天气暖和的时候,我能恢复得更好,那么到那时候,由你决定吧。”在婚前的日子里,他们从未间断过书信来往,几乎每天都要写信。她终于接受了勃朗宁的爱,因为这是她生命的唯一机会。她后来在《葡萄牙人十四行诗集》的第一首中写道:
我想起,当年希腊的诗人曾经歌咏:
年复一年,那良辰在殷切的盼望中翩然降临,
各自带一份礼物分送给世人——年老或者年少。
当我这么想,感叹着诗人的古调,
穿过我泪眼所逐渐展开的幻觉,
我看见,那欢乐的岁月、哀伤的岁月——我的年华,
把一片片黑影接连着,
掠过我的身。
紧接着,我就觉察,
我背后正有个神秘的黑影在移动,
而且一把揪住了我的长发,
往后拉,还有一声吆喝:
“这回是谁逮住了你?猜!”
“死。”我回答。
听哪,那银铃似的回音:“不是死,是爱!”
——方平译
命运仿佛是一场恶作剧,当她以为是死神来临的时候,来到的却是爱神。她在诗中说:“年复一年,那良辰在殷切的盼望中——简直是望眼欲穿,然而却从天而降。”对巴雷特这样的女子来说,爱情不止是生命的光,更是她的宗教。爱不仅能够拯救她的灵魂,也拯救了她的身体。可以说这是一个奇迹,一个卧床24年之久的女子,居然在爱的力量下站了起来,重新回到阳光下,不但能够像正常人一样行动,也获得了正常人所拥有的一切,包括孩子。没错,她不但是一个妻子,还是一个母亲。做母亲是所有女性的天然权利,任何人也无权剥夺。
成为勃朗宁夫人并不容易,父亲对这桩婚姻自始至终都是反对的,尽管巴雷特和勃朗宁的意志如此坚决,但仍然遭到包括父亲在内的众多人的反对,最终,巴雷特与勃朗宁决定效仿他们喜欢的诗人雪莱,准确地说是像雪莱夫妇一样——私奔。
1814年,无法见容于英国社会的诗人雪莱,在政治上和诗坛上都遭到多方面的排挤,情感上也受到挫折,便携16岁的女友玛丽私奔意大利。为了避免来自世俗社会的压力,勃朗宁和巴雷特秘密举行了结婚仪式(当然没有得到巴雷特父亲的祝福)。父亲因为他们私定终身,甚至剥夺了巴雷特的财产继承权(不过事后,她仍获得了属于她的那部分的继承权)。
之后,勃朗宁夫妇迅速离开英国,分头前往意大利的比萨,在那里会合。1849年,勃朗宁夫妇移居意大利中部的佛罗伦萨,他们的儿子小罗伯特也在那里诞生。
生活本身即诗歌
移居意大利后,勃朗宁夫妇几乎每天都在一起,简直像初恋的情人一般难舍难分。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的中心,米开朗琪罗、达·芬奇、拉斐尔、提香、但丁等巨人曾长期在此活动,这里有大量的历史遗迹,包括美术馆、博物馆、书店和文艺沙龙。勃朗宁夫妇不但在这里建立了新居所,还结识了很多新朋友。
他们的居所分为上下两层,一楼是餐厅、会客厅、客用洗手间以及夫妻两人共用的书房。二楼是卧室、婴儿室、浴室、洗手间和专供勃朗宁夫人做身体恢复训练的一间练习室,还有一间勃朗宁夫人专用的私人小书房。除了参加社交活动,勃朗宁夫人经常一个人在专用书房里阅读和写作。
勃朗宁知道妻子在写诗,但对其创作的内容完全不了解,因为这是妻子的秘密。勃朗宁夫人每次完成作品后,都非常小心地将诗稿藏好。直到有一天,勃朗宁正站在窗口看着街市上的风景,忽然感到妻子从后面抱住了自己,将一卷诗稿放进了他的口袋。勃朗宁夫人不允许他回头,叫他等自己离开后再看,如果觉得不好就丢弃掉,然后逃也似的朝楼上跑去。
勃朗宁打开诗稿,是十四行诗,是专属于爱情的诗歌。他只看了一半就激动得叫了起来,这是自莎士比亚以来最出色的十四行诗。他兴奋地朝楼上奔去,紧紧地抱住了妻子。
勃朗宁夫人用她诗的语言将两人的爱情之路写了出来,从最初的犹疑、不安,到内心的喜悦和快乐。她的作品是如此饱满、丰盈,洋溢着内心强烈的爱的力量,与大多数爱情诗歌中充斥的畸情、伤情、煽情相比,简直算得上一种“爱情教育”范本,是可以给青年男女当爱情教科书的作品。那么酣畅淋漓,却又不虚饰造作,堪称英语诗歌中璀璨的语言宝石。
勃朗宁夫人认为这些作品仅仅属于对方,是纯粹的私人化的东西,是自己对丈夫最高的爱情回报。但勃朗宁认为这些诗歌太棒了,不该只属于他,应让所有读者都看到。当然,最初发表这些诗歌的时候,勃朗宁夫人并未使用真名,甚至连这组诗歌也用了一个掩人耳目的名字,叫作《葡萄牙人十四行诗集》,仿佛这些作品出自一个外国人之手。
对于有些人来说,爱情只是柴米油盐醋的内核,而对于有些人来说,爱情却是生命。勃朗宁夫人无疑是一个视爱情为生命的人。或者说,爱情还是点燃希望之火的种子,使她从死神的阴影下逃脱,并将所有的心曲写到纸上。至于勃朗宁,他是这样一个男人,他对勃朗宁夫人不止是情感上的心心相印,还有对她全身心的守护。
东奔西顾在《妖孽也成双》中说,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如此温暖过一生。勃朗宁和勃朗宁夫人具有很多相似的特质,他们都富有激情,拥有丰富的内心和蓬勃的生命力,勇于冲破世俗的羁绊,从属于自己的本心。勃朗宁夫人敏感、羞怯,勃朗宁温和、从容、果敢,他们就像是从同一块大理石上切割下来的部分,有着温和的花纹和相似的纹理。
当他们处于不利的环境中,即便是在父亲反对,近乎被家族驱逐的情况下,他们依旧选择了爱情。爱情不止是生命的黏合剂,还是生命的归宿。他们如此离不开对方,以至于连上帝都给予恩赏,使他们在意大利建立了爱情的宫殿,并始终完美。尽管勃朗宁夫妇崇拜雪莱,但勃朗宁与雪莱不同,他才华横溢,同时温柔、善解人意、始终如一,而雪莱却善变,甚至于三心二意。所以说,他不只是她的爱人,还是她的守护天使。
勃朗宁夫人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更是一个诗人。她随时在体验,或者说她的生活本身就是体验。她把生活当作诗歌,或者说生活只是诗歌的现实体现。在生命的前期,她用古希腊和古罗马诗人留在时间长河里的文字来对抗黑暗。在生命的后期,她用诗人激情的笔书写自己的生活,在尚属保守的维多利亚时代,她将自己的情感纳入了文学史。与大多数作家或者诗人不同,她不是把自己的生活当作写作的材料,她的目标不在于构建文本,而在于“自己”,生活本身即诗歌。这使得她的诗歌有一种我手写我心的朴素,平白浅近,文字激情澎湃,感染力很强。对她来说,如果说只有一个读者,那就是勃朗宁,真正的读者只有他一个人。
她的诗歌中不仅写满“爱情”,更是对勃朗宁的写实。她渴望他、记挂他、想念他,却又怀着忐忑。我们在这些文字里找到了一种心灵的真实,一种女性对具体的人的文字性的“重建”。两个相爱的人分处两地,他们通过想象和思念来完成对彼此的灵魂的认知。
同时,当一个人在面对另一个具体的人时,内心其实也在对应地构建另一个灵魂。我想起日本作家太宰治说过的一句话:渐渐地,我开始想念一个人,想得不得了,想看见他的脸,想听他的声音,想得不得了,好像是腿上扎着滚烫的针灸,只能忍耐着不动一样。
勃朗宁夫人的很多诗誉满诗坛,其中我最喜欢的一首叫作《我的棕榈树》。她在这首诗中写道:
我想你!我的相思围抱住了你,
绕着你抽芽,像蔓藤卷缠着树木、
遍生出肥大的叶瓣,除了那蔓延的青翠把树身掩藏,
就什么都看不见。
看着你、听着你,
在你阴影里呼吸清新的空气,洋溢着深深的喜悦时,
我再不想你——我是那么贴紧你。
所谓世间,不就是你么
这样爱一个人,那是怎样一种痴迷。被一个人这样爱着,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这首诗中激扬的爱,远远超出了勃朗宁夫人那单薄的身体。泼辣,酣畅,像燃烧的火、决堤的水,完全消解了文字和生活之间的距离,不是书写在纸面上僵死的文字,而是带着某种声音和气息,仿佛是面对面地表达和触摸,是一种血管里的澎湃声,打破了英语诗歌中的那种优雅,令人想起中国的一首民歌:世上只有藤缠树,人间哪有树缠藤。树死藤生缠到死,藤死树生死也缠。
对于树木这种植物,不论是产于东方的落叶乔木还是西方诗人笔下经常出现的棕榈树,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高大,生命力旺盛强悍,是男性的象征。藤是一种柔弱的植物,是女性的象征,这种象征带着一种生命的坚韧和执着。高大的树木生命力旺盛时,它缠绕着;高大的树木成为一截枯木时,它依旧缠绕着,就像彼此拥抱的两个人。树木也许会因丧失生命而失去活力,但是藤在干枯后仍旧保持拥抱的姿态。就像勃朗宁夫人描写的:“看着你、听着你,在你阴影里呼吸……”
诗歌的表达不同,但是内核相同,千百年来,不同民族的人的情感内核也没有太大区别。《血色浪漫》中,钟跃民和秦岭在信天游中唱道:
一碗碗个谷子两碗碗米,
面对面睡觉还呀么还想你,
只要和那妹妹搭对对,
铡刀剁头也不呀后悔。
孤独在勃朗宁夫人内心形成的冰冷内核,只有爱情才能溶化。一旦这个内核化开,就像是金属溶液一般炽烈。她为了与勃朗宁结合,不惜与父亲决裂,私奔意大利,确实有一种铡刀断头而不悔的义无反顾。她用爱情来报答爱情,用独立的自我面对至爱的人。
从勃朗宁夫人的作风来看,她更像一个现代主义女性。她阅读了欧洲大量古典作品和思想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力作。她寻求独立,不只是在经济上和精神上,还包括在生活上。她要求自己有独立的生活空间,专注于写作和阅读,保持部分心灵的秘密。她不从属于任何人,在爱的前提下,她只属于他——勃朗宁。她的爱是炽烈的、毫无顾忌的、健康的、旺盛的,甚至是不留余地的。
1861年,勃朗宁夫人去世了,她安静地躺在爱人的怀里。就像电影《返老还童》中那样,一生爱着一个人,不论是神采照人还是年华逝去,最终死在爱人的怀里,像婴儿那样安静。勃朗宁夫妇一起生活了15年,他们几乎不曾有过分别,几乎日日都在一起。就连临终前,勃朗宁夫人还在和丈夫讨论夏季旅行计划。也许她只是倦了,想在爱人的怀里睡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