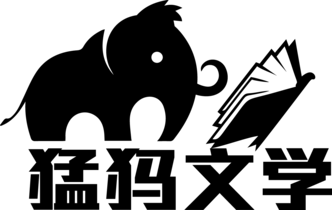第6章
西蒙娜·德·波伏瓦(1908年1月9日—1986年4月14日),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创始人之一,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与萨特、梅洛·庞蒂共同创办《现代》杂志,1949年出版《第二性》,成为女性主义经典。小说《名士风流》获龚古尔文学奖。
波伏瓦说:“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21岁的波伏瓦,以其特有的敏锐和智慧,取得法国哲学教师资格考试第二名,就足以证明这话不只是说说而已。那场考试的第一名是萨特,他们的名字就这样联系在一起,精神也开始结合。
第一次见面,波伏瓦就给萨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我认为她很美,我一直认为她的脸庞足够迷人,不可思议的是,她既有男人的智力,又有女人的敏感。”心意相通的人才容易成为朋友,两人很快单独约会。长长的散步,停不下来的谈话,他们在一起能谈论的东西太多了,人生、哲学、文学、前途……这样的契合让两人都欣喜不已。
毕业后,萨特要去军队,所以不得不分别,他们许下承诺:在分别的日子里,我们虽然不在彼此的身边,但要一直保持一种亲密的关系,不许欺骗对方,而且要对对方无话不谈。但是,萨特还提出一个近似荒谬的要求:他不会和她结婚,而且,他要尽其所能地得到所有的女人。这样的要求肯定会吓坏一般的女子,但波伏瓦欣然同意了,而且后来,萨特要求和她结婚时,她也拒绝了。
只有我们在一起,我才是我自己
当人类经历了“一妻多夫制”“一夫多妻制”“多夫多妻制”的社会,终于将“一夫一妻制”固定停留下来,这被称为最科学、最安定的组合模式,可是,“一夫一妻制”真的是最科学、最好的生活状态吗?钱锺书用一部《围城》对“围城”内外的男女极尽讽刺,《爱杀17》用自身的堕落反击父母的貌合神离,《无法忍受》里的几对夫妻忍受婚内监狱般的折磨,我们不由得怀疑,当下的婚姻模式是否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束缚?
到底有没有更好的、更符合人性的组合方式?没有哪一种人际关系的形式是不可改变的,也没有哪一种人际关系的形式是不可能创造出来的。当大多数人听之任之的时候,萨特与波伏瓦提出了一种尝试:共同建设一种自由、平等、相互信任、相互给予的超越传统的爱情关系。他们订立了一项契约,两人将永远情投意合,并且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这种关系,同时双方保证各自在生活、感情和性的方面享有充分自由,条件是永远不隐瞒和撒谎。
这是对三纲五常、基督天主的挑战,先不论结果如何,终究是为自由而战。既保持了各自的独立,也避免了因婚姻的静止性带来的厌倦。波伏瓦说:“我们毫不怀疑地根据自己的意志行事,自由是我们唯一遵循的原则。”
此后,他们确实保持各自的独立,尊重各自的生活和情人,虽然大部分时间处于分分合合的境地,但是他们对彼此的感情却没有像很多婚姻中的感情一样“厌倦到终老”。
人是容易厌倦的动物,但是婚姻并不是解决厌倦问题的最佳途径。就像治水,需要的是疏通,而婚约大多数时候用来填补那堵不稳固的土墙。
50多年来,他们之间没有发生过大的摩擦,虽然期间也有过嫉妒、责问,但彼此都知道那些情人只是激情的产物,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只有他们之间的爱情才具有世俗的超越性。有一次,波伏瓦写信追问萨特与一女子的关系,萨特回信说:亲爱的海狸,和她们在一起时,我感到很快乐,但只有我们在一起时,我才是我自己。
波伏瓦有过一个强劲的情敌,是德洛丽丝·费奈蒂,萨特曾想不顾与波伏瓦的约定而跟她结婚。波伏瓦为了报复他,与芝加哥作家纳尔逊·阿尔格伦暧昧。她与阿尔格伦真正经历了一场只有彼此的恋爱,他为她买了一枚银戒指,她一直带着。如此,波伏瓦与萨特的关系便摇摇欲坠了,但是她还是回到了巴黎,萨特也放弃了费奈蒂。
在没有婚书保障的情况下却坚持到最后,这是思想上的共振,感觉上的共鸣,以及心灵上的互相需要。波伏瓦写道:“我们不发誓永远忠诚,但我们的确同意延迟任何分手的可能性,直到我们相识三四十年的永远的年代。”
这有赖于两人坦诚相对,赤裸对话,对对方毫无隐瞒。这既是人格的力量,也是极度信赖的结果。
他们是阅读对方作品的第一人,互相激励,彼此成就。事实上,波伏瓦对萨特的付出完全超出了妻子的概念,他们的关系远远超过了婚姻。在萨特生命的最后10年中,他的身体一直很差。中风、神经错乱,认不清身边的人。从那时起,波伏瓦减少了自己的写作,每天照顾他的生活。萨特在弥留之际用不连贯的话称波伏瓦“妻子”,并不断地表达他十分爱她。
后来,在回忆录中波伏瓦写道:“遇见萨特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萨特也多次向外界表示:“波伏瓦是上天给自己最大的恩赐。”
1980年,萨特去世,法国为其举行国葬。波伏瓦作《永别的仪式》,并在萨特的墓志铭上写道:他的死使我们分开了,而我的死将使我们团聚。6年后,波伏瓦去世,法国同样为其举行国葬。
1999年,法国通过了一项法律:男女只需办理契约合同而不用办理结婚手续,亦可成为契约式的生活伴侣。
这无疑是对两位大师生活方式的肯定,法国,这个浪漫的国度对他们做出了最好的纪念。
我爱她,但我和你在一起
萨特一直视波伏瓦为最理想的精神对话者,他喜欢对她说:“我们的结合是一种本质上的爱。”
什么样的爱才可以称为本质上的爱呢?我一直认为维系爱情或者维系婚姻的有四条线:物质线、习惯线、情感线、精神线。
大多数人被物质线联结在一起,合作规律、习俗观念、原始欲望,比如相亲。
一些人被习惯线联结在一起,在一起习惯了,依赖了,离不开了,比如学长和学妹。
还有一些人被情感线联结,因爱慕而接近,因接近而日久生情,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
极少数人被精神线联结,心灵相通,志趣相投,在精神上相互吸引,彼此需要,比如萨特和波伏瓦。
越往后的联结越牢固,直至不需要任何契约。
马斯洛说:某些人是做较为抽象的思考,因此,他们自然先会想到统一性、整体、无限性和其他诸如此类的概念;而另外一些人的精神则是具体的,他们往往考虑着健康与疾病、利润和亏损,他们创造了圈套和悲剧,他们几乎不对别的知识发生兴趣,他们总是试图去劳作、付酬、治愈。
获得第四种爱情的人只能是马斯洛所定义的抽象思考能力的人,所以是极少数。大多数是平庸,极少数才是精华。
但是,萨特和波伏瓦的爱情也遭到了非议,甚至有人把《危险的关系》说成是影射两人肮脏行径的书,其实这本书写于18世纪,比他们的出生都早了两百年,从这明显的诽谤可见,超出常规的生活为多少人所不齿。
电影《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也把这种理想拉到一地鸡毛的境地,面对如此不堪,也有人说:何苦要这样拍他们呢?
我一直崇尚他们不用婚约维持的爱情,唯美、浪漫,却被电影撕下面具,还以为是为了自由,其实不过是为了标榜自由。一个是身体的囚徒,一个是思想的囚徒,在自设的束缚和标签中挣扎。很难想象写出《存在与虚无》的萨特会是这样的一个人。当他明白存在即此刻的时候,他就享受此刻,毫不伪装,原来真实的他是这么个小丑模样,不过是芸芸男人中的一枚。
男人的劣根性都能在他身上体现,却因着才华的优势,被涂上一层神圣的色彩;而波伏瓦——女人即是女人,不是变成了男人才能显示平等,而是彻底回归女人之美,把女人之美放在与男人同等的位置上才是平等。伍尔芙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对。波伏瓦莽撞得有点像萧红,不知其所以然,一生好像都在赌气。把贪婪包装成自由,不过是彼此的垫背。我玩累了的时候还有你,你玩累了的时候还有我。这根线似乎不那么牢固了,嫉妒,恐惧,分离,最后再在一起,却不是因为爱情,不是因为心有灵犀,不是因为心与心的需要,却是因为那张“伟大”的合影。
我认为《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这部电影一定有“诽谤”的成分,但在对男女角逐战场的描述上,女人处于劣势因素的分析却有一定的道理。
当得知萨特和德洛丽丝·费奈蒂相爱,且深感他们无法分离时,波伏瓦忍不住问萨特:“你爱我还是爱她?”萨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爱她,但我现在和你在一起。”她深感绝望,为了抵抗这种绝望,波伏瓦写作《第二性》,这是一本被誉为“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甚至被尊为西方妇女的“圣经”。
这本书涵盖了哲学、历史、文学、生物学、古代神话和风俗的文化内容,可见波伏瓦的博学多识、清晰的逻辑和丝丝入扣的辩证能力,纵论了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历史演变中妇女的处境和地位,女性总是处于从属地位,受到男性和社会的束缚。但是这种束缚不是从来就有的,不是上帝或者什么伟大力量规定的。波伏瓦在书中说:女人是生成的,是在男权社会下变成女人的,是男人给出了这个“第二性”。
陷入爱情中的男人和女人是有区别的,男人可以将性、爱、婚分得清清楚楚,可女人正如波伏瓦所说:当女人倒下的时候,注定是要受奴役的。她要冲破这种奴役,摧毁这种文化偏见,达到与男人同等的自由状态。
《第二性》出版后,同是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加缪谴责波伏瓦“败坏法国男人的名誉”;一个作家还专门写信到她与萨特办的《现代》杂志社,对她进行恶毒的攻击。“淫妇”“性贪婪”“性冷淡”“女同性恋者”等恶毒的谩骂四处飞扬,萨特在自己的公寓里遭到了袭击,波伏瓦被保护起来,《现代》杂志被查禁,两人不得不躲起来。
但是这本书一周卖了两万册,波伏瓦瞬间扬名,毫不逊于萨特。她一点不在乎自己引起的公愤,甚至蔑视地说:“人们把我塑造成两种形象,或是个疯子、怪人,或是个女慈善家、女教师,但没人说过这两者不能协调,我可以是一个有头脑的荡妇,也可以是个不正经的女慈善家。”
《第二性》是女性觉悟最彻底、最有力的一本书。波伏瓦在书中说:“女人并非为其所是,而是作为男人所确定的那样认识自己和做出选择。”她们失去了主体意识和自主性,除了男权社会的压制之外,更多是由于她们自己在无意地制造自身被贬低的结果。
萧伯纳说:“如果锁链会带来敬重,那么给人套上锁链比去掉他们的锁链更加容易。”资产阶级女人看重自己的锁链,因为她们看重阶级特权。而我们的社会中的女性又因何如此呢?当马克思把劳动的权利赋予女性时,久而久之,这种权利成了令人讨厌的徭役,一种想用结婚摆脱劳动义务的想法与做法产生了。当她们用美貌和温柔去取悦男性时,就被物化为他者,靠自己对男性的价值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有头脑的女人刻意取悦,会变得拘谨,她对取悦于人感到难受,她不像她奴性十足的小姐妹,取悦他人完全出于自愿,但这往往只会刺激男人,而不能驾驭他们。尽力谋生的女人比将自己的意志和愿望埋在心底的女人更加分裂。
她在最后一章叙述了走向解放的独立女人,她们仍旧处在一种限制中,却也乐观地指出:历史事实不能被看作确立了永恒真理,它只不过反映了一种处境,这种处境表现为历史,因为它正在变化。”
这种处境何时终结,女性何时才能像男性一样,成为自为的存在,用自身的行动证明自己的意义?在21世纪的今天,大多数女性已经有自己的工作、事业,能够做到经济独立,为什么仍旧难以获得本质的幸福,即心灵的自由?
波伏瓦在给出明智之见的同时,忽略了女人先天已有的东西——性别的天然差异。她在这一点上的忽略,让她陷入某些事物的矛盾中、言行的无法统一中以及自我怀疑的折磨中。
看清生活的真相,然后爱它
真正的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收放自如。
在梅里美的“卡门”面前,波伏瓦是多么拘谨、扭捏,因为她心存爱情。爱情不但让人卑微,还让人失去自由,比婚姻更具破坏性。对于爱情,对于婚姻,对于终身伴侣,她也有过美好的设想:“我们共同攀登高峰,我的丈夫比我稍稍敏捷、强壮一些,他常常要助我一臂之力,与我一级一级地向上攀登。我的丈夫既不比我差,也不超出我许多,他保证我很好地生活,但不剥夺我的自主权。”
这种自主和并肩让她选择了她所倾慕的、风流的、只注重当下的萨特,只是这种选择没有让她一味被动地接受、认同他的男权思想,而是成了一位坚定的“女权主义”者,这是认识的结果。正如很多年后,面对身患癌症的母亲,她又开始产生了另一疑问:为了“自由”是否就可以抛弃一切血缘和温情?
这个时候,她是否想到了曾经挚爱自己的情人纳尔逊和克劳德?大概只有经历过残酷的人生,看到真相后,才能真正反思生命真义。
她借笔下人物之口说出:“没有什么比自己的生活更真实了。只是那真实总是无法言说。人们憋得太久,难免会有些一反常态的表演。让一切更虚幻。”晚年的波伏瓦是怅惘的,她终于感到有些事情在逻辑上说得通,真正实行起来却倍加艰难。
因为那个时代的医学还不发达,她对性别的认识有其局限性,在爱情这个难题面前,她只看到了事物的表象,却没有深入本质。她在《第二性》中写道:“他想要这个女人的那一刻,他热烈地想要她,只想要她,因此那一刻是绝对的,但那只是一刻的绝对。女人受愚弄,过渡到永恒。可是男人的欲望是激烈又短暂的,它一旦得到满足,很快会消失,而女人往往在产生爱情之后,变成男人的囚徒。”
如果男人长久地依恋女人,这并不意味着你对他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正是她所要求的,她的退让只有在恢复威望的情况下才能挽救她,不可能逃避相互性的作用。因此,她要么必须受苦,要么就必须自我欺骗。她把男人的爱情想象为她给予他的爱情的准确对等物。
有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这种可悲的境况,比如尼采说:“女人的激情作为对各种自身权利的完全放弃,恰恰要求异性身上并不存在的同样的感情、同样放弃的愿望。因为,如果两者都出于爱情而自我放弃,说白了,结果会产生我说不清的东西,也许可以说是对空无的恐惧吧?女人愿意被控制……她于是要求有人占有,要求他不要奉献自身。”难道真如莎士比亚所说: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
波伏瓦竭力摒弃这种论调,以为超越文化就可以达到尼采所谓的意志自由,直到20世纪80年代,医疗技术证明,男女差异不仅仅是父权文化造成的。
在实验中,男性和女性的大脑是有明显差异的,经过适当的刺激,它们会在不同的区域“闪亮”,这些实验揭示了独特的神经活动过程。经发现,男性和女性大脑的“硬件”是有明显区别的,这些差异和荷尔蒙因素印证了男性和女性的行为及态度特征是不同的这样一种传统观点。
我们认识到这种差异,是想更好地做出理智的选择,而非听天由命,认为机体都如此安排,女人是劫难难逃了。我们应该在波伏瓦的认识基础上,利用尼采的超人精神,然后像伍尔芙所说:与男性联结,让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地生活和工作。”
“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成了自然的本质,人的行为成了自然的行为,那么就达到了自由的高度,男女最终应该超越自然差异,建立友爱关系。这一马克思的美好愿望,是否能够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