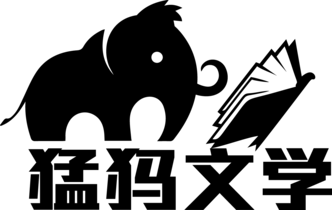第1章 卡米耶·克洛岱尔
序言:因独立而完整,因自由而健康
1876年,法国赠自由女神像给美国,纪念美国独立100周年。如此创意,大约只有法国人才能想到。他们对自由的重视远超对道德的维护,也最早认识到,道学家们将道德作为枷锁,实则是在扼杀人性。
从平等,到独立,到自由,标志着文明在进步,无论种族、阶级还是性别。其中,性别是最为原始的分化,最自然的形成。多少年来,社会文明对女性的压制,甚至使得女性自身都认同自己是“第二性”,只有少数女性觉醒了——波伏瓦看清了这个事实,杜拉斯打破了这个规约,伍尔芙否定了这个定理。女性主义者如雨后春笋,在法国先冒了芽,然后波及英美,再艰难辗转,传入中国。
中国的女性,在一种虚假的、局限的平等中寻求自由。已经极端“物化”的女人,误以为物质的积聚就是获得自由,控制了男性就是掌握平等。她们把这些当作目标,忧心忡忡,疑神疑鬼,成了感情和物质的奴隶。其实,心灵若无自由,人便不是完整的,仍是附庸。
许多自诩“成熟”的女人,炫耀自己“驭夫有术”,男人如何听话,如何成功;而另一些女人抱怨男人窝囊、花心、不负责。她们的重心仍是男人,不懂得自己也是一个完整的人。《蜗居》《宫心计》《婚姻保卫战》等影视剧风靡一时,《男朋友不发朋友圈,就是不爱你》《年薪百万的男生喜欢怎样的女孩》等鸡汤类文章大行其道,大龄未婚的女子被称为“剩女”……宣扬独立自主的女性,其实仍是依附者,正如一句电影台词:走得太快,灵魂跟不上了。
即使在现代社会,婚姻也被大多数人视为最高等的幸福,有这种想法的传统女性并不自由,她们视“妻子”为唯一职业,还要把那些自尊自爱、追求独立的女子拉下来,与她们一起被奴役,否则就被称为“出格”,被视作“异类”,被抨击,被防备。无论事业多成功,只要没有成为“妻子”,就要领受怜悯的目光。连蒋方舟这样年少成名的才女,都会说“过了27岁,在婚恋市场上就变成被挑选的对象”。
爱情没有退而求其次
诚然,爱情是美好的。独立不意味着敌对,自由不等同于自私。伍尔芙在强调女性要“成为自己”时,不代表愤怒地与压迫女性的社会切断联系,与导致女性丧失主体意识的男性断绝关系,而是向社会开放,与男性联结。她觉得最正常、最适合的状态是男性和女性这两种力量在一起,和谐地生活和工作。
爱情,当然要。
只是在某些爱情稀缺的土地上,追求爱情的姿势就显得有些尴尬和无奈。比如,《聊斋》,看得多了,就成了同一个故事:一个书生,恋上一个狐妖,不能长相守,狐妖临走时再送来一个美女,书生见美女而忘狐妖,他们从此过上和和美美的日子。套路大多如此。怪不得有人说,中国文人自古缺乏终极价值追寻的精神,不是黄金屋便是颜如玉,最多不过为民请命。
因循至今,大多电视剧亦是如此。两个男喜欢一女,女人选择一位。编剧心疼男二号,顺手再拉一个女生。男二号倒也听编剧的话,很快便移情。
韩剧《来自星星的你》,结局是男主角回到另一个星球,没有拜托男二号好好照顾女主角,他说的是:“别乘虚而入。”面对阻隔,女主角一直在等,男主角一次次努力回到地球,原来真正的爱情没有借口,爱你,千难万险也要和你在一起。没有你的日子我无法忍受,更无法想象没有我的日子,你是何等孤单。他说:“我在另一个星球,一个人就算活得再久又有什么意思。”爱情,从来没有退而求其次,不能在一起,一万个理由都是借口,真相只有一个:就是不够爱。
中国人总能理顺自己的心,没有红玫瑰、白玫瑰也可以,不像西方人,决绝、彻底,以死相搏。或许是现实,或许是懦弱,张爱玲早早看透,中国是一个爱情荒芜的国度。自古少有梁祝,多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有点贤德,有点美色,即可。
真正的独立,是生而为人的独立
前段时间,看了些讲禅修的文章,谈到婚姻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关系社会安定、家族子嗣传承的大事。似乎婚姻与爱情无关,爱情甚至成了扰乱婚姻的因素,因为它会变,不稳定,扰乱人心。至于如今离婚率飙升,有人说,女人应该服从男人。巴尔扎克说:“排除了爱情的婚姻制度必然导致女性通奸。”他以讥讽的口吻劝告丈夫严加看管妻子,如果他们想避免名誉受损的可笑场面,就不要让女人受教育、有文化,必须禁止她去做一切能让她发展个性的事。
看《非诚勿扰》《中国式相亲》等综艺节目,发现现有的婚姻模式都只是在上演一出出聊斋而已。误把占有欲当爱情,以为婚姻就是后半生的保障。
基于物质,也终于物质,至于爱情,寻不到。
鲁娃写过一篇小说—《寻找三色旗》。法国人,崇尚爱情胜过生命。这篇小说充满幽默对答和机智回应,在法国那所尊贵的公寓里,上演颇具中国特色的夫妻冷战情节,倒是有趣得很。
魏明回到家,拄着拐棍,提了一条打了石膏的腿,样子已经够滑稽了,却偏偏面前站了一个穿着他睡衣、睡裤、拖鞋的法国男人—他的同行,律师。
“这么说,你不是来讨论案子的。”魏明简直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那个法国男人笑起来,“您不是想问我,会不会带您的妻子私奔吧。如果她愿意,我会的,我喜欢与她在一起,就这么简单。”
魏明被激怒了:“她是我的妻子,我爱她。”
法国男人仍旧微笑着:“您虚伪,如果您爱她,就不会留她一个人过圣诞了。”
我想鲁娃是借法国男人之口,指出中国男人的通病:虚伪!她鄙视他因了自己那点小成绩而沾沾自喜,眼光只停留在地位、身份、房子上,明哲保身,绝不会为了朋友或者正义去打一场官司。而此时,魏明也厌恶了她:“十多年在一条船里撑,都是看走了眼。”他又说:“你觉得我像是有快感吗?哭还来不及呢!”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婚姻。
故事最后,她离开了魏明,这场中国式婚姻在法国告一段落。我有时会想,如果不是在法国,而是在中国,这场婚姻会不会轻易结束?那个独立的女子会不会思考生命的价值、爱情的真谛?是否会有一个法国男人让她看到另外的选择?
人类异化为物,扭曲,病态,失去了自然的、健康的美,受制于道德、规范与传统,给自己缚上神圣的枷锁。而女人更为可悲,还要受制于男人,受制于婚姻,甚至受制于其他女人。不过总有那么几个人,在浩浩荡荡的沉睡中苏醒,比如萨特和波伏瓦,他们的“协议式结合”引领了以浪漫著称的法国男女婚姻模式。1999年,法国通过一项“亚婚姻”立法:男女只需正式办理契约合同,而不用办理结婚手续,即可以成为契约式生活伴侣。
真正的女性独立,是作为“人”的独立,而非谁的妻子,谁的情人。“被异性挑选”不是独立,“驭夫有术”也不是独立。只有独立的女性才会懂得:美满的婚姻从不基于物质,它只和爱情有关。
卡米耶·克洛岱尔(1864年12月8日—1943年10月19日),法国雕塑大师罗丹的学生,也是罗丹的情人和艺术竞争者。她倔强、任性,又才华横溢,拜罗丹为师,很快坠入爱河。因难以忍受罗丹的不忠,最终与他分道扬镳。贫困孤寂的生活,世人对其作品的冷漠,使卡米耶绝望。她打碎了自己心爱的作品,被送入精神病院,在那里度过30余年的光阴。
“这样的女子,很痴情,但也很麻烦。”我指着《大话西游》里的紫霞仙子,对一个朋友说。他说他想要的爱情,是与一个女子一同赴死。我想,爱到愿意同死的地步,也就没有必要去死了,与有情人做快乐事,岂不更美。但我望着他嬉笑的眼睛,才觉得上了当。他想要的不是一起死去,而是愿为他死的女子。只有这样的女子,才能给占有欲过强的这类男人渴求的激情,给予他们那颗贪婪的心以充分享受。外表沉静优雅,内心却狂热似火,卡米耶就是这样的女子。内心激烈,带着势如破竹的力量,刺戳着男人懦弱又贪婪的内心,让他们无处可躲,只好狗急跳墙,摒弃全部。
罗丹是一个内心脆弱且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在卡米耶面前,他几乎是恼羞成怒地退避,又摆出一副赢家的嘴脸,其实最后输得很难看。他的选择昭示着他浮泛和懦弱的心性。他觉得自己只能与一味退让的萝丝匹配而不能与聪慧尖锐的卡米耶并行。他已经老了,或者说他从一开始就老了,拖着疲惫的身躯,对青春的力量既畏惧又好奇。
照片上的罗丹胡须浓密,体格强健,给人一种专注、威严的感觉,但也隐隐地透露出一种忧虑。据说他的童年很压抑,父亲老来得子,对他非常器重和宠爱,希望他能够成为警官。他却喜欢鼓捣一些当时看来属于下三烂的东西,学习成绩极差。父亲对他越来越失望,动辄便拳打脚踢,企图矫正他的“胆大妄为”。这让他从小就自卑、恐惧,缺乏安全感,以至于患上了一种叫作强迫症的心理疾病。他严格把控自己,事事要求完美,看起来很自信,然而内心是极其不安的,因为一个真正自信的人不需要这么谨小慎微,会表现得更加洒脱。
罗丹可能就是被这种不安推着去征服世界,征服女人。在雕塑界他成了大师,而他占有过的女人也不计其数,卡米耶最终不过是他占有的其中的一个。卡米耶向他要求爱情,却不知道他这类人是不懂得或者经不起爱情的,尤其是激烈的爱情。
卡米耶是早期女权主义者,却成了被男性及艺术等级世界迫害的牺牲者,她坚定地表达自身欲望,相对于萝丝而言,她代表着一种觉醒。
这世间凉薄,你温暖如河
1883年,19岁的卡米耶被老师布歇先生托付给罗丹。卡米耶向罗丹要了一块大理石,想为弟弟保罗雕刻一尊半身像。在这个家里,除了父亲,卡米耶最爱的就是弟弟保罗,他虽然很年轻,却能写出不同凡响的好诗。为了感谢罗丹,她同时雕刻了一只青筋微露的脚送给了罗丹。这个作品让罗丹当即决定让卡米耶做他的助手,参加美术馆纪念门厅的大型雕塑工作。
那天,卡米耶正在脚手架上工作,无意中瞥见罗丹用暧昧的动作摆弄他面前体态丰腴的裸体女模特。卡米耶惊呆了,晚上回到家里,她对弟弟保罗说不想再去罗丹那里了。
第二天,她果然没有来。罗丹一早就打听卡米耶的消息,他的助手建议再雇一个,罗丹说:“不!”他亲自去找卡米耶。那时候他已经感觉出,卡米耶是无可替代的。罗丹的登门拜访使卡米耶心中的不满消散无踪,她又回到了罗丹的工作室。当她为裸体模特摆姿势时,罗丹看出自己花了许多年才弄通的东西,卡米耶无师自通了。
那个时候,上帝并不眷顾罗丹。他的生命在嘲讽和攻击中行进着,灵感近乎枯竭,再加上雨果的死,他感到生命正在枯竭,面对模特毫无灵感。或许是看到了他眼神中的枯寂和孤独,卡米耶代替了裸体模特。
她丰润如白玉的身体和青春的朝气重新燃起了罗丹的激情,他情不自禁触摸她,狂吻她。他们谈论艺术,讨论雕塑问题,也做爱(似乎艺术家的灵感时常要靠女人的身体来激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借口),她成了他的缪斯女神。卡米耶既是一个美好的情人,又是一个理性的伙伴。她的存在修正了罗丹对女性的看法,因此罗丹以女性为题材的作品也多起来,艺术创造力有突飞猛进之势。他身边形形色色的女人来了又去,只有卡米耶突显成一个重要的角色。
但卡米耶没有料到,日后罗丹会给她的生活和创作带来烦恼和痛苦,甚至是灾难。起初她在罗丹的工作室为他无休止地工作,充当他的模特,罗丹以此创作了《加莱义民》《地狱之门》和《沉思》。后来罗丹功成名就,工作室的订单接踵而来,罗丹不得不开始交际和应酬,很少再参与石坯粗刻等最初几轮工序。
擅长雕刻大理石的卡米耶与罗丹共同完成订单任务,但以她署名的作品很少。至今流传下来的罗丹的作品里有多少卡米耶的心血不得而知,不过可以确定,他们是互相影响的。比如罗丹的《加莱义民》和卡米耶的《手持麦穗的女郎》,几乎是相同的雕塑,是同时创作的,没人分得清到底是谁抄袭了谁。
卡米耶与罗丹的关系进一步升华。罗丹想操控卡米耶的灵感和思想,而卡米耶也想融入罗丹的生命。这一时期是甜蜜的,从罗丹的作品《永恒的春天》《吻》《亚当》和《夏娃》可以看出,他所焕发的青春以及她所彰显的活力都融入他的作品中。
《吻》中的女人自然是卡米耶,男人是罗丹自己。这件作品取材于但丁在《神曲》里描写的弗朗切斯卡与保罗的爱情悲剧。罗丹取用这一题材并以更加坦荡的形式塑造了一对不顾一切世俗诽谤的情侣,在幽会中热烈接吻的瞬间。里尔克说:“情侣的热吻给人一种遍布整个雕塑的感觉,如同太阳升起,阳光洒落到每个角落。”由此可以看出罗丹压迫性的力量和卡米耶竭力向上的支撑。
为你,千千万万遍
与罗丹在一起的10年间,卡米耶很少把精力花在自己童年时的梦想上,鲜有自己的创作。为此,一直宠爱她、支持她雕塑事业的父亲感到了不安。他提醒卡米耶不能只为罗丹而活,不该过多地与罗丹抛头露面。他在担忧卡米耶的未来,不只是事业,还有生活,因为罗丹有一个相伴几十年的伴侣萝丝,虽然没有正式结婚,但如家人一样,他们还有一个儿子。他怕卡米耶陷进爱情的旋涡,受到伤害。
记得有一次,父亲回家,卡米耶去车站接他。进家门之前,父亲塞给卡米耶一些钱。这一幕让正站在楼上窗口张望的母亲看见了,母亲哭哭啼啼地把自己关进里屋,骂家里人合起来骗她,为了一个疯疯癫癫玩泥巴的傻瓜,大家一起受罪。母亲既不理解也不支持卡米耶的梦想,甚至对她有些冷淡。
卡米耶为了罗丹几乎与家人闹翻。她很少回家,住进了罗丹在巴黎近郊买下的佩安园。这个临时的家更像工场。她在这里拼命地干活,把满腔的热情和灵感都献给了罗丹,沉浸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家里,很少与家人和朋友联络。
卡米耶全家要去维洛夫度假,父亲不顾女儿的反对邀请了罗丹夫妇。罗丹应邀而来,也是为了让卡米耶尽快返回巴黎,因为他要雕刻雨果和巴尔扎克像。他需要卡米耶带给他灵感,让自己能够把这两位大师的神韵展现在各自的脸上。
当罗丹夫妇出现的时候,卡米耶发现,萝丝才是人们眼中罗丹的伴侣。萝丝也对卡米耶产生嫉恨,歇斯底里地烙伤了怀孕的卡米耶,并将她赶出罗丹的工作室。卡米耶并没像个泼妇一样去争夺,而是要罗丹自己做出选择。罗丹思虑着说:“我不能像打发仆人一样赶走萝丝。她像只小动物一样地依赖我。”他希望能保持现状,而卡米耶只能做他的情人。此时,卡米耶才意识到父亲的话是多么中肯,罗丹对她没有尊重,没有把她当成一个平等的人来看待。罗丹从来不付工资,也不付做模特的酬劳,看起来更像供养情妇。罗丹给予她的位置,给予她的这种生活方式激怒了她,卡米耶终于在1898年正式与罗丹分手。
眉头解不开的结,命中解不开的劫
天才的女人需要灵魂的撞击,罗丹就是卡米耶遇到的灵魂。而艺术家处处寻找美,卡米耶就是美的化身。但是灵魂的互动是一生一世的事情,而美的冲击只是暂时的迷恋,所以两个人的感情从一开始就是不对等的。罗丹是卡米耶一生的劫难,卡米耶只是罗丹生命中的一个阶段。
原本以卡米耶的个性和才华,她会拥有杰出的艺术成就,却在爱情上摔了跤。至情至性的人,从来不是以理智为生活准则的,所以没有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任其疯狂,哪里还有做事的精力。
身为女子,卡米耶是渴望正常的、完整的、温暖的家庭生活。她试图将精神生命之爱,转化成生活之爱,可是她输了。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同等重要,有几个人能坚强到只生活在空中楼阁?每个人都需要精神上的安慰,也需要感情上的安慰,需要真诚的、踏实的、有尊严的陪伴,但是卡米耶生命的激情之火被生活冰冷的泪水淹灭了。为情所伤的人,很容易叫人心疼,所有旁观者的安慰都没有用,那些无关痛痒且道不着正题的话都是风凉话般的高调。
痛苦和耻辱让卡米耶扑进父亲的怀里哭泣。她曾是父亲的希望,她却让父亲失望了。
家人为了她的雕塑梦搬迁到巴黎,如今又搬回了维洛夫,弟弟保罗远走他乡,整个世界都弃她而去了。卡米耶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像一座雕塑,木木的。时间能够治愈的伤口算不上伤口,卡米耶的痛苦不仅有失去爱人的痛苦,还有自尊被践踏的耻辱,幸好她还有雕塑。
只有雕塑不会抛弃她,她像抓住救命稻草般开始埋头雕塑。
也许她一直需要的是父亲给她的溺爱,但是罗丹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像父亲那样让她依赖。罗丹对情人是征服和占有,而不是爱。罗丹对卡米耶充满激情,因为他可以征服她。但在激情之外,罗丹需要被人照顾。卡米耶给不了他所需要的照顾,只有萝丝才可以永远包容他,照顾他。他的自私需要无私来填充。
当卡米耶能够燃起罗丹的创作激情时,他就源源不断地索取。当她要求得到相应的回报时,他唯有退缩。她把才华与感情投注在他的身上,过于孤注一掷,所以结局很惨。当她企图自救的时候,为时已晚。虽然与罗丹决裂,但是她并没有走出感情的阴影,仍旧在自己的情绪“沼泽”里游荡。她的作品《祈祷者》《哀求》《吹长笛者》带着一种凄婉情愫,而《命运之神克劳索》《波尔修斯和蛇发女妖》又透露着仇恨和挣扎。
卡米耶的雕塑中只有恨、痛苦与折磨。雕刻不再是她艺术上的享受,反而成为宣泄的工具。她选择离开是为了保全自尊,但是情感的力量太强大了,吞没了她的自我。有人评价说她只凭一股悲愤的力量创作,没有上升到对整个生命的洞悉,缺乏人性的灵光。但是我认为悲愤的力量达到极致时,也能创作出个性的东西,由痛苦凝结成的、扭曲变形的造型也是一种自我的表达。她竭力表现自我,虽然有些空乏无力,但也有可取的价值。
在曾经深爱卡米耶的音乐家德彪西(因为罗丹的嫉妒,他们终止了彼此的关系)的帮助下,她的作品终于正式展出。不知为何,在展会上,她故意打扮成萝丝一样的庸俗女人,浓妆艳抹。或许这也是痛苦的宣泄,是行为艺术。人们对这些扭曲变形的作品毁誉参半,赞誉的那一部分归功于罗丹。这又是一个打击,正如弟弟保罗所说:“罗丹做梦,你做工。”她再次孤独地躲进自己的世界。
在你放弃他的时候,他又会偶尔记起你的好,所以罗丹登门了。但是这种登门拜访并不是他的爱意回归,而仅仅是来此缅怀一下。卡米耶果断地把他拒之门外,此时的她已疲弱不堪,经不起风吹草动。
巴尔扎克全身像的成功使罗丹再次想起了卡米耶,才有了上述的登门拜访,男人就是这样,以为别人爱他,就会永远爱他,可以随时利用一下这点爱,却不能体会恨的感觉。所以罗丹对陷入疯狂的卡米耶的谩骂很是吃惊。
卡米耶真是疯了,怀疑自己所有的不幸都是罗丹在搞鬼。当房东提出要收回房子时,卡米耶悲愤地冲到罗丹家,用石头砸他的门窗,吼叫道:“罗丹,从你的狗窝里给我滚出来,我究竟爱你什么呀!”
卡米耶成了罗丹的竞争对手,她的创作灵感非常旺盛。而罗丹却枯竭苦坐,失去了卡米耶,不能再驾驭卡米耶,使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嫉妒。当世人指责卡米耶时,他保持缄默。不但如此,他还直接剽窃卡米耶的作品,所以卡米耶对他的愤恨到了崩溃的边缘。
卡米耶得了妄想症,她曾经美丽的脸变得扭曲,只剩下了慌张的神色。她以为罗丹要迫害她,以为来买她作品的人是罗丹派来的。她大喊大叫,装出强悍的样子来掩饰内心的恐惧。她用大锤毁了自己所有的作品,把当初为罗丹制作的独脚雕塑扔进了塞纳河。
1913年,父亲离世,但没有一个人告诉她这个消息。
不久,卡米耶经医院鉴定患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由母亲签字,把她送进精神病院。母亲在给精神病院院长的信中说:“是她自己宣判了自己的死刑。”卡米耶在精神病院里,一次次恳切地给弟弟保罗写信,希望能早日离开这个折磨人的地方:“别把我扔到这儿,我多么想回家和你们住在一起。看好我的东西,不要落到罗丹手里。他很害怕我出去,并会千方百计地阻挠。我好想回家。你被流放的姐姐。”最终,她在精神病院度过了30年的凄凉余生。
左岸柔软,右岸冷硬
在当时的法国,雕塑事业是男人的艺术,所以卡米耶不被重视。她不善交际,默默无闻的处境把她带入一片死寂,她的作品也一直在表现这个主题——内心的孤独感。经历了人生的沧桑,她开始怀念童年生活,在大自然的寂静里捕捉生命存在的瞬间。其实她与罗丹有很大的不同,罗丹表现理念的东西,卡米耶表现原生生活,在变化中寻找永恒。
艺术批评家阿斯兰曾经说过:“尽管不是同时雕塑完成的模特儿,也不是同一个年龄段的保罗,但是它们具有同样的眼神、同样的力量和同样的信念,这个女人的观察具有奇妙的穿透力。”卡米耶在雕塑中能够从素材中抽取永恒的东西,把不同的东西融合成一个整体,使作品简洁、平衡。她与弟弟保罗在艺术上有共通之处,看到了对立面的和谐,外在与内在的交融。
卡米耶的雕塑以人物为主,起先是受法国画家布雪的影响,结构平衡,人物表情内敛。与罗丹认识后,主要创作两性情爱的作品,如《华尔兹》中人物大幅度偏离重心的舞姿诠释着圆舞曲的旋律,将舞曲中情侣沉醉的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再现两人相爱时的甜蜜时光。
她的《成熟年代》创作于与罗丹感情结束之时,作品中跪下的女子是卡米耶请求罗丹不要离开的一幕,生动地勾勒出他们那一段情感纠葛。
卡米耶的挣扎始终没有让她拜托罗丹的阴影,现在人们提起她时总是冠以“罗丹的情人”,连布鲁诺·努坦执导的电影《CamilleClaudel》在中国也被译作《罗丹的情人》,影片中,在卡米耶最后一次的作品展示会上,她装饰华丽妖异,满脸涂着厚厚的脂粉,带着无助绝望的眼神穿过人群,却只剩惊愕和茫然。“无可比拟的绝代佳人般的漂亮前额,美丽无双的深蓝色眼睛,性感却又倨傲倔强的大嘴。除了小说封面画中的人物的眼里以外,你很难再在别处找到那样的蓝色……身披美丽和天才交织成的灿烂光芒,带着那种经常出现的,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残酷的巨大力量。这样的美丽,她曾经尝试用这样的美丽来守住爱情,却最终束缚了自己。”这是保罗对姐姐的描述。
有人说:“婚姻的胜者是罗丹,24岁时结识萝丝,50年后有了一纸婚约。生活的败者是罗丹,40岁时遇见卡米耶,15年后他们形同陌路。”那一纸婚约是用多少屈辱换来的。只是对于萝丝这样的女人而言,是感受不到屈辱的。何况这婚约从来不代表爱情,或许只能说是恩情,表明她的付出总算有了回报。罗丹说:“总不能像个女佣一样把她踢开吧。”如此交换,卡米耶做不到。她可以为艺术献身,却不可以为爱情献身。她要求平等,她看到了罗丹的改变,她鄙视他。
卡米耶是最让我觉得心痛的女子。爱情和理想也曾是我生命的两大主题。多年后,当我像《地图上的年轮》中的女子一样,淡漠地想起往事,感觉一切都不值一提,沧桑的记忆仿佛前尘梦境,已经失了真。
但我仍在思索:当一个女人疯狂地爱上一个并不爱她的男人时,该如何自救?似乎从来没有自救的方法,全都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幸存者大多是那些浮游的、贞静的、不够爱的女子,这似乎成是无解的难题,像哈姆雷特徘徊在“tobeornottobe”之间。就像尼采说的那样,看透的人总是不行动。也许我们应该看透,跳出爱情,站在高处,去看明白这一切是多么虚妄。
当罗丹在遗嘱中说,要给卡米耶留一展厅时,我流下眼泪,为这最后的“施舍”。
为爱情而失去自我的女子总不能让我喜欢,但是卡米耶却让我一次次情动潸然。当她在精神病院里,写信给弟弟说“我的小保罗,你会在五月底会来看我吗”时,我的心狠狠地疼了一下。她曾为爱情痴狂,却从未卑微。她是凌厉的,有孤注一掷的叛逆和狂傲。这是一种人格的力量,一种爱的力量。如此结局并不是她的错,而是时代的错,世界的错,男人的错。
错误的时代,错误的地点,当这个世界还没有准备好,一个女天才便突然降生了。如果早一点,她就能像乔治·桑那样以浪漫主义为保护,更自由地生活。如果再晚一些,她也会碰上20世纪20年代的变革。她就是生在那样一个让人尴尬的时代,一个不小心便跌进了深渊。烟花散尽,不过是一场寂寞的表演。